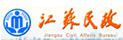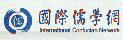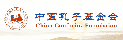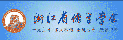|
作者简介:陆永胜(1978—),男,河南南阳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阳明学)、美学、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摘要:王阳明“良知”思想的新向度诠释是新时代文化自信建设的重要价值观念资源之一,道德、价值与信仰是当代文化语境中王阳明良知图式的三重向度,三者各有侧重地分别呈现于学术、政治和生活话语语境中而又相互关联,构成了当代文化以阳明学为视阈的内在认知结构。道德向度的良知作为一种道德理性是理想之善和现实之善的统一,也是对人的本质的确证,其中内含着价值确认;良知的价值属性以道德属性为基础,表现为道德向度的“善”“恶”向价值向度的“好”“坏”与“是(对)”“非(错)”的转化;良知的信仰向度基于对人之德性与价值的肯定,追求超越层面的自我实现,并在“幸福感”上找到道德满足与价值关怀、个体追求与社会认同的交汇点。当代文化语境中良知意蕴的新阐释,是对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体现,有助于新时代的文化建设。
关键词:王阳明;良知;道德;价值;信仰
王阳明的心学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的论断已众所周知,但目前的研究多在理论宣传层面,学术思想层面的研究尚少,特别是深层次的价值观念向度的汇通研究更少。作为具有时代性特征的课题,阳明之良知与当代文化在价值观念层面相契合的向度研究在根本上是阳明学的当代诠释话题。当代话语言说的阳明学是当代文化语境中的“新阳明学”,这涉及到文化语境和文化生成的关系问题。当代文化语境可概分为学术话语语境、政治话语语境和生活话语语境,每一种语境对文化的塑造是具有倾向性的,抑或说,语境对文化的生成是有诉求的。文化生成即是文化的意义言说,它要表达的正是语境的诉求。在此意义上,文化语境和文化生成具有相互建构的作用,文化语境形塑了具有特定特征的文化,文化的特性强化了特定领域的文化语境。同样,阳明学在当代不同语境的诠释中呈现出不同的意义言说图式,道德、价值、信仰是其在学术、政治、生活三种话语语境中分别呈现出的意义向度,这三种向度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然而又隐而不显,亟待探讨的理论内涵。
一、道德向度:学术话语语境中的良知图式
学术话语语境有相对宽泛的内涵和外延。本文主要讨论哲学学术话语语境,即学术界以文本为基础、以形上哲理思辨研究为内容、以历史上的思想理论为资源的研究语境。作为泛称的“学术界”在具体存在样态中是有空间性的,这就造成了学术话语语境具有一般普遍性和区域个体性的特征。当代中国哲学学术话语的言说方式受到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双重影响,因此,良知的当代话语结构图式是不同于古代传统哲学的,但也不完全等同于西学的哲学范畴,这主要体现在其意义的生成上。阳明继承和发展了孟子“不虑而知”的良知,它不属于认识论、知识论的范畴,而是属于修养论的范畴,具有内在的价值属性。这种内在的价值属性体现为价值观念或价值原则,它是道德意识的最为核心的内容。因此,在中国哲学的学术话语语境中,良知话语结构图式是侧重于道德向度的。
一般认为,中国哲学整体上呈现为伦理学形态,但“伦理”一词在中国是西学东渐以后才出现的,而“道德”一词在中国古代哲学本是两个概念,“道”指普遍的法则或存在的根据,具有本体论或形上的意味。“德”指“道”在现实中的具体化,即道所指的普遍原则或存在根据在实践中得到了具体的规范或规定性。因此,“道”与“德”虽具有形上与形下之别,但在本质上二者是一致的,体现了中国传统“体用不二”的逻辑思维。与“用”相关,道德关乎礼,礼是道德规范的体现,但严格说,礼是德的体现,其本质是道。那么,“伦理”一词与其的相契之处在哪里呢?在西方哲学的语境中,道德的内涵包括权利学说和德性学说,而伦理学的讨论对象仅为德性学说;在康德那里,道德所包含的权利和德性都指向应然,具有形上意义,而在黑格尔那里,伦理学所讨论的德性更多地关注现实之维。可见,中西方哲学语境虽有不同,但道德一词包含着形上(理想之维、应然)和形下(现实之维、实然)两个层面是一致的。当代语境中的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中国传统哲学中“道德”之“德”的一面。同时,在内在观念上,中西方语境中的“道德”也有一定的一致性。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德”之“道”具有生而有之的天赋意义,所谓天赋,具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既然是天赋,无论其内涵,落实于人,就是具有形上根据的价值或权利;另一方面,作为形上的天道,其内涵是至善的,所以落实于人的德性也是善的。前者和康德之道德的权利观念具有一定的一致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天赋的权利肯定了每一个人都有内在的存在价值,表现为一种价值原则。后者和西方哲学语境中道德的德性学说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道”的理想之善和“德”的现实之善及二者的统一与西方语境中德性的理想之维与现实之维及二者的统一可以做到一定的呼应。在当代中西方哲学融合的话语语境中,这体现为一种相对一致的道德观念,即人之为人和人应得到尊重的根据。道德的价值原则由个人走向社会整体,最终体现为政治、制度、法律等的内在根据,这一点后文另有论述,资不赘述。德性指向人的存在,道德之至善则与人的本真意义上的存在相关,因此,道德在本质上是人存在的一种方式。这种存在方式与价值、信仰密切相关。王阳明的良知正是在此意义上与道德的内涵更趋于相近。
良知是阳明心学的核心概念,体现为多个层面的意涵。首先,良知体现为一种本体,即良知与“心”与“理”是一,这是确立良知的“至善”性质的重要前提。阳明说:“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初不能有加损于毫未也。”[1](P68)“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肯定了良知之“善”的性质。“未发之中”“寂然不动”既表明作为本体的良知的本然状态,又表明良知之“善”是本体之实然。“人人所同具”则肯定了良知作为人人具有的圣性的永恒不变和普遍性。“不能有加损于毫未”是对良知的先验道德性再次确证。可见,本然良知之“善”是具有普遍性的。由此王阳明才认同“满街都是圣人”,这种提法肯定了良知是每个人成圣的内在根据,同时也突出了人的道德的主体性和道德主体的内在完满性。
其次,良知是先验的,但又离不开经验,这担保了良知的理想之善和现实之善及二者的统一。阳明继承了孟子先验良知说,认为良知是先验地植于人心的。“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1](P77)在阳明看来,从本体的角度出发,良知既不同于见闻,也不由见闻而产生,良知是具有先验性的,二者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但良知和见闻并非没有关系,阳明认为感性认识是良知的发用,二者是体用关系。良知不会因见闻而受到滞碍,但良知的呈现又离不开见闻。值得注意的是,阳明对良知与感性认识关系的讨论是在道德范畴内展开的。
再次,良知是一种道德理性,具有认知和评判的能力,这是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德相统一的重要体现。作为形上之道,良知具有普遍性品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具有普遍价值的道德标准。同时,良知的先验性和本体性担保了这种道德标准的永恒性与正当性。作为形下之德,良知具有个体性品格,体现为个体的能动性,它可以知善知恶、为善去恶,具有判断善恶的能力。在阳明看来,良知之知是自然而然的,良知之用即是仁之发用。“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便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实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2](P7)可见,良知的理论效力及实践能力范围都是在道德领域内被言说的,这和阳明一贯的圣人立场和圣人之德的标准是一致的。阳明说“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3](P826),即是肯定良知是人人具有的,不可更移的,它是人成圣的根据。当良知成为每个人成己、成圣的根据之时,其道德的维度便是很明显了。
可见,良知在阳明心学体系内的地位与性质决定了其道德的维度,从道德的视阈出发,良知的道德内涵是什么呢?王阳明在“四句教”中讲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4](P129)在阳明看来“良知者,心之本体”,[1](P67)心即良知,心体无善无恶,即是良知无善无恶。所谓“无善无恶”者何?“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2](P31)“至善者,心之本体。”[4](P106-107)“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2](P28)肯定了无善无恶的至善内涵。同时,阳明也为良知至善内涵提供了形上担保,那就是“理”,“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1](P78)良知即“天命之性,粹然至善。”[5](P268)良知之谓至善,在于其为天理。从“天理”的形上意义来讲,良知的“至善”内涵可谓是其形上之维,是理想之善,是其内涵的究竟义,故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此外,阳明并不否定良知的现实之善,“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发用上也原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恶的。”[4](P126) 伴随着良知之发用,良知的理想之善亦落实于实践中。在实践中,理想之善呈显出来,便是现实之善,理想之善被遮蔽而没有呈显出来,便是恶,便是不善。在阳明看来,善与恶并不是一对相对的道德范畴,恶之根源在于良知被遮蔽,“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也。故善恶只是一物。”所以,恶并不“否定”善,更不“否定”良知。相反,恶是从反面对良知的现实之善的肯定,以及对良知的理想之善的本质确认。因此,良知不但在形上层面是至善的,在形下层面也是唯善无恶的。从体用一源的角度言,良知的理想之善和现实之善就可以较好地对应并统一起来。在此意义上,主张良知既有善也有恶,或良知既无善也无恶在根本上都是一样的逻辑认知错误,是不恰当的。显然,在当代中国哲学话语语境中,道德向度是良知话语结构图式的应有之义。
二、价值向度:政治话语语境中的良知图式
政治话语语境在古代主要体现于政统观的表达,在当代则体现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表达,二者既有联系,亦有区别。当代政治话语语境中的良知图式和观念文化的政治倾向性、导向性密切相关。“无善无恶是良知”,良知的“至善无恶”性质是本有的、不可移的,这担保了良知之善是一种普遍永恒的正面价值。当良知与当代观念文化的政治倾向性、导向性遭遇时,在某种意义上对后者具有正面规范性。这种规范性是一种内在规范,它在道德向度为良好政治提供保障。因此,从价值形态看,政治的价值诉求是基于道德之善的正面价值诉求,而不是负面的价值诉求。这其实是在有意识地提醒我们,我们讨论的是观念形态的政治,而不是现实政治。观念形态的政治可以超越现实政治,跨越国家、种族、制度、区域的界限,其价值诉求也因此具有普遍性。
良知的道德属性内含着价值确认,故其也具有价值属性,并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作为规范与制度的道德基础;第二,作为个体和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的价值标准。良知的道德向度的“善”“恶”内涵在这两个方面发生了意义引申,于前者,良知之“善”“恶”与价值规定的“好”“坏”相联系,进而体现为符合道德应然要求的规范与制度则为“好”的,反之,则为“坏”的。于后者,良知之“善”“恶”与价值评判标准的“是(对)”“非(错)”相联系,从而体现为符合价值评判标准的观念与行为则是“是(对)”的,反之,则是“非(错)”的。因此,政治话语语境中的良知图式的价值属性是建立在道德向度的基础之上的。
良知之为规范与制度的道德基础是以其普遍性品格为担保的。在现实层面,规范与制度的确立有两种目的性:功利目的和德性目的。前者以利益为评判标准,后者以人与社会的道德发展为评判标准。在中国文化的视阈内,后者显然是第一义的,也是终极目的。良知与规范、制度的关系有两方面的规定性:首先,良知对规范与制度的局限性规定,即一种“度”的规定性。如王阳明说:“圣人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然他知得一个天理,便自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4](P106)节文度数显然不是客观的礼乐名物,而是观念形态的规范与制度,它以天理良知为前提和基础。良知对规范与制度的局限性规定,就是要把规范与制度限定在一定的界限内,保证它的合理性,以及它是被道德所允许的。当规范与制度在道德的界限内,从价值规定的角度判断,它就是“好”的规范与制度,反之,规范与制度超出了道德的界限,就是“坏”的规范与制度。
其次,良知对规范与制度的应然发展的方向性引导。良知的发用与生活世界密切相关,规范与制度的展开亦是如此。在现实生活中,规范与制度的展开呈现为运作的过程,只有在运作过程中,良知的基础作用才能够发挥。如果规范与制度只是作为文本存放起来,则无所谓“好”与“坏”。运作过程在表面上呈现为规范与制度的使用,实质是良知的道德属性在生活世界的发用,抑或说是良知由本然良知向显在良知的转化过程,这一过程既可以体现为个体行为过程,也可以是社会整体行为过程。从积极的意义讲,符合价值规定的规范与制度有利于个体和社会形成“好”的习惯,并演化为相对自觉的过程,进而积淀为优秀文化;从消极的意义讲,不符合价值规定的规范与制度则容易导致个体与社会行为的失范与越轨,甚或价值观念的混乱。道德是人的本质的确认,生活世界离不开人的参与,体现为运作过程的规范与制度的运用自然也离不开道德的作用。在阳明学的视阈中,良知不但重新建构了意义信仰本体,而且重新确立了价值主体,良知因此而具有本体-主体地位。在此意义上,良知既是对人的内在价值的确认,也是对人的社会价值的确认,既肯定人的自我实现的意愿,也肯定人与人之间坦诚认可的存在意义。所以,以良知为视域,社会规范与制度的良性发展必将是符合人的发展的,也是符合道德价值规定的。只有以良知为价值导向,才能消解规范与制度对人的异己性。因此,在现实生活世界中,“好”的规范与制度必然以良知的应然要求为导向,从实践层面看,良知之于规范和制度不仅仅是内在的道德基础,而且是一种评价的价值标准。
在阳明学的视阈中,良知是一个既存有又活动的范畴,言良知即包含着致良知。王阳明说:“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6](P223)“知者行之始, 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 知行不可分作两事。”[2](P14)知行合一是阳明良知思想的内在维度。阳明在晚年只说良知,而少讲致良知,即是基于这一思想维度。良知的这种特性同样也体现在其价值向度中,从“知”的角度言,良知的价值体现为内在的价值观念,从“行”的角度言,良知的价值体现为事事为为的外在价值标准。在王阳明那里,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是良知的一体两面,内外合一的。
从价值形态看,作为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的良知内涵与良知作为道德基础的“好”“坏”内涵是不同的。“好”“坏”并不等同于“善”“恶”,原因在于:第一,“善”“恶”是良知本具的性质判断,“好”“坏”是良知所发之“用”的评价判断;第二,良知之“善”“恶”本是一事,良知之“用”之“好”“坏”是对“用”是否符合德性要求的判断,抑或说,是对符合度的判断。良知作为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同样是以“善”为基础的,但已经转化为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这种价值观念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群体都是认可的,这种价值标准不管是对个人还是社会群体的评价都是同样标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是对认可度的评价,得到认可的则是“是(对)”的,反之,则是“非(错)”的。由此,良知之“善”“恶”引申为“是(对)”“非(错)”。阳明心学是对当时知行不一、知而不行的社会弊病的针砭时弊,救治的良方即是良知。王阳明站在圣人的高度对世人提出的致良知之方,其实是严格的道德主义。王阳明强调“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4](P106),即是以严格的道德主义严厉摒除有违真正道德的私欲恶念。所以,在阳明这里,当良知落实于社会生活现实,仅作“善”“恶”的判断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引申为“是(对)”“非(错)”的判断。王阳明对此亦有论述:“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4](P121)“这些子看得透彻,随他千言万语,是非诚伪,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4](P102)在王阳明看来,好好色、恶恶臭是良知之自然,当“是”“非”等同于“善”“恶”,那么,对“善”“恶”之“好”与“恶”的道德情感评价就转化为“是”与“非”的价值判断。其实,从良知出发,“是”“非”基于“善”“恶”,二者具有一定的内在一致性,但从判断“万事万变”的角度出发,“是”“非”的标准就是绝对的,因此,“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而判断“是”“非”的标准是良知,方法在于看是否合于良知,“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从此意义上言,“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王阳明在这里成功地以“是”“非”判断取代了“善”“恶”判断,从而由道德论域向价值论域转换,显示了其心学的绝对主义立场。而这种绝对主义在王阳明那里则体现为政治、伦理、学术的绝对主义。
良知作为个体和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的价值标准,在个体领域成为个体对所处社会形态、规范、制度、秩序等做出合理性和正当性判断的依据,进而指导个体行为协调,外化为个体交往原则。在公共领域则在社会历时发展中成为一种文化认同,而在社会共时发展中成为各社会阶层、各民族的社会共识,当文化认同和社会共识不发生错位的现象,完美融合,价值观念才能外化为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标准,并能够对社会整合产生积极的作用。
总之,在价值视阈内,良知的内涵得到了丰富和扩展。良知的价值向度是其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发生关联的重要联结点。
三、信仰向度:生活话语语境中的良知图式
良知作为价值观念内化于人的意识,构成人的基本价值认同,同时,良知作为价值标准外化为人的判断根据,具体化为个体原则和社会规范。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统一于以人为中心的生活世界中。从人的本质出发,生活世界不是客观的人、事、物的混合体,而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人的意义所及之处。在阳明学的视阈内,生活世界即是良知(人)的意义世界,也是德性的世界。因此,生活话语语境以对良知(德性)的确认为前提,以对人之价值的肯定为中心,以人的终极关怀为目的。
人与生活世界的密切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克服了生活的异己性、无序性,意义的绵延贯穿整个生活世界,因此,生活话语在一定意义上即是以人(良知)为中心的意义言说。生活话语语境是与学术话语语境、政治话语语境相对而言的,指的是二者之外的话语形态。当代生活话语语境呈现出多元化,如行业分工导致生活话语的群体差异,区域价值认同差异导致生活话语的地域差异等,但随着科技发展、世界一体化进程推进,生活话语语境日益向趋同化发展。生活话语语境在历时和共时方面具有特殊性,但在一般意义上,它关注的是人作为个体和类两个方面的生活状态。从文化的层面看,人的生活状态要摒弃物质的多样性,而注重精神与文化的层面,注重个体的整体性,具有一定的形上意义。因此,生活话语语境并不能截然划分为个体的或类的,从形上意义来讲,它或可说是类的精神文化状态的个体表达,体现为一个时代的追求或信仰。
在阳明学的视阈内,生活在本质上是意义的表达,而且体现为实践过程,可以说,生活是意义和实践过程的统一。良知是生活意义的赋予者,也是实践活动的主导者和评价者。王阳明说:“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1](P49-50)“事事物物”本是对象性的“物”(包含实践意义的事之对象化),“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即通过“赋义”的过程将外在之物涵化为心内之物,事事物物之理即是良知,故心与理一。心与理一是王阳明于此论述的重点,但“赋义”的过程让我们看到良知对意义和实践的主宰作用。于此我们可以看到,良知在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及其在生活话语语境中的基础作用。但与良知的道德向度、价值向度不同,生活话语语境中的良知图式更多地体现出信仰向度。基于生活本身的浑融性,生活话语语境中良知图式的信仰向度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对个体存在价值的确认,这主要体现在实践层面。生活本身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人以自身的劳动能力参与并创造这一过程。人是实践过程的主体,离开了人,实践过程便不存在。在此意义上,实践过程不但是一个感性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理性的意义过程。人在此过程中首先确认了人自身的存在,其次意识到人之为人。因此,生活话语便离不开对个体存在价值的确认和对个体生活的感受。在阳明学的视阈中,良知是不离于见闻的,良知对感性生活的肯定自然也包含了对人存在价值的肯定。王阳明站在圣人的高度提出了“医世”的药方——致良知,但他并没有放弃普通人。“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1](P54)“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4](P117)“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4](P128)在王阳明看来,圣人与愚夫愚妇同具良知,而且愚夫愚妇作为普通人的社会群体,他们的认知还构成了判断“异端”的标准,甚至与人讲学,也须以普通人的身份方行得通。这就在人的本质层面和社会存在层面分别肯定了愚夫愚妇的存在价值。甚至在作致良知功夫方面,虽然王阳明认为“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1](P54),但在具体的功夫设计中,他还是为普通人保留了入圣之途。“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4](P128-129)“利根之人”“其次”,其实都是普通人,他们都需要不断作圣学功夫,方能成己成圣。唯有不同者,他们各自的功夫入手处有所差异。其实,在功夫差异的背后,王阳明仍然肯定了普通人本具的内在“圣性”——良知。所以,良知不但是人(普通人)之为人的根据,也是人之为圣的根据,抑或说,良知是人由此在走向超越的根据。故良知对于人的存在而言,不但具有本真义、现实义,而且具有超越义,这正是对人的存在价值的全面肯定。
第二,对真善美的追求,这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的追求。良知是至善的,在中国哲学中,真、美与善是统一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其实是一种境界形成和提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逐渐达到对自身的觉解和对世界的精神把握,展示出人所理解的世界图景,呈现出个体精神升华的不同层面,其中融入了人的道德理想和人生追求。
在阳明学视阈中,真并不是指知识论的真,从修养论而言,良知之真侧重于自我在德性上的实有诸己,从本体论而言,良知之真侧重于本心之诚。前者关涉功夫,后者关涉本体。功夫上的实有诸己强调功夫的真实切己,此已是心学实学的范围。王阳明强调“事上磨练”“体究践履”“实地用功”等等已有明显的价值论导向,所以,功夫层面的良知之真和良知的价值向度密切相关。从价值的层面看,良知功夫之真一方面指向修身成圣,一方面指向家国天下,在儒学视阈内,后者以前者为基础,是前者由己及人、向社会领域的延展,而前者是最根本的,这也是阳明良知学的本色。
显然,在良知学的意义上,“真”主要不是指客观存在之“真”,而侧重于意义价值的“真”,如“君子之成身也,不惟其外,惟其中;其事亲也,不惟其文,惟其实。”[7](P1108)这种“真”既是道德情感之真,同时也是主体人性之真。作为本心之诚的“真”具有“真实存在”的意思,即人的存在本体——心的本来的存在状态,“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4](P120)作为存在意义上的诚,它是天道之本然,能覆载万物,成就万物。“诚是心之本体,求复其本体,便是思诚的工夫。”[2](P38)本体通过功夫而达到的本然状态即是“真”的状态或“真”的境界。处于诚境的人按其真性而呈现,故事亲则孝,事兄则悌,事君则忠,事友则信,呈现出一种德性之美。这种以“诚”为最高原则的功夫体验,体现出主体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正是良知之真的价值意义所在,体现了“真”作为追求目标的信仰向度。
良知之“善”在性质上侧重德性之至善,在内容上指中国传统哲学的“仁”。“止于至善”即是“为仁”,是修养功夫的最高追求。“为仁”即是对善的追求,善是目的理性的体现。在儒学中,善和美是统一的。至善之境不仅仅是“君子”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人生境界,也是一种审美境界。实现仁的境界,首要的即体现为对“至善”的追求。“至善是心之本体”,良知“无所亏欠”的呈现就是仁的境界。“至善”作为天理的规定,一种“宇宙力量”,它不仅仅是道德规范和道德力量的根源,而且也是一种必须服从这些规范的绝对命令。[8](P84-85)故王阳明认为真知必能行,“知而不行,非知也”,而且这种服从是一种自觉自为的服从,故当人与天相感应的时候,他也就处于“天意所定”的状态,达于真正的仁境。
在宋明理学家看来,仁是“心之全德”(冯友兰语),“仁包四德”(朱熹语),因此,仁的意义就具有绝对普遍性,仁(善)与美、真一样,来自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在心灵与物事的现实合作中显现出来的。在王阳明看来,仁不能从外在事物中去求取,而应从“心”与“物”的自然相感中去求取,这种自然相感既表现为“心”的自由(宜),又表现为“物”的自然(无人伪)。只有在此前提下,仁的境界一旦由心灵中实现出来,则能使天下皆善、天下皆仁,从而出现一个和谐统一的世界。[9](P190)
可见,在阳明学视域中,对善的追求不仅仅是个体的精神追求,而且体现为以良知为基础的意义世界的建构。这里不仅涉及心与身的关系,而且涉及心与物的关系,这正是我们在当代文化建设中要处理的人与己、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的关系问题。
当真、善作为追求目标,臻于境界时,便和美密切相关。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美”是和“善”统一的状态,是主体的情与理在体验过程中呈现的结果。美的境界是一种自适自得的境界,它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所谓合目的性即意味着对人的存在价值的确认,所谓合规律性即意味着对理的普遍性的尊重,这二者正是阳明良知说的应有之意。所以,在阳明学的视阈中,美是以培养道德人格为出发点和目的而进入审美言说的,并反过来,又把审美视为建构道德人格的一条有效通道。从本质上说,道德与审美都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二者在深层次上的人性、人格之解放与人的自我完善上,具有同构性和比邻性。如“万物静观皆自得”就是一种通过审美观照获致道德品格的方式。这种对理想道德人格的追求方式,要求通过审美的方式来体验生命,通过道德的方式来强化生命,这样不仅可以张扬人的生命自由价值,而且可以显示人类生命价值的自由理性精神。[9](P119)在阳明哲学中,其所强调的道德原则,同时也是一种审美原则,美是一种具有真的品格、善的性质的美。
真善美统一于以人为中心的日常生活之中,是日常生活的精神升华。在阳明学视阈中,生活内在于以良知为内涵的意义世界之中,人对真善美的追求,体现了良知在生活语境中的信仰向度。
第三,对自我实现的追求,这主要体现在超越层面。良知作为存在,不是抽象的、玄虚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它是即本体即主体的存在,这一方面表现为良知作为精神实体的本体存在,它是道德、价值、信仰之所从出,另一方面表现为良知的自觉能力,它的具体落实即体现于具有良知践行能力的个体和类(社会群体)。前者表现出良知的至善性和自在完满性及这种性质外化的内在本然要求,这种“内在本然要求”既可从致良知的功夫向度来理解,也可以从传统儒家“推仁”的伦理向度来获得理据。而“外化”的过程即是实践的过程——呈现为个体和类对至善性和自在完满性的双重追求。至善性在内涵上包括真善美,从实质的意义上看,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内含着道德情感的满足,即道德的幸福感。自在完满性体现为意义的充盈,对意义充盈的追求即是对人生最高价值的终极关怀。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至善性是自在完满性的基础,也是其一个向度,抑或说,人的自在完满性离不开道德的完满,但又不止于此,比如价值的实现等。意义的生成(赋义)过程即是生活实践的过程,个体和类都将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并在此过程中追求自我的实现和超越。
生活实践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当下存在境遇的不断评价和超越过程。在阳明学的视阈内,人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人的良知对外物具有认知和评价功能,在逻辑上,良知又是评价标准的内在原则。因此,从良知出发,人对物的评价原则和评价标准是统一的,这是由良知的普遍性原则决定的。在王阳明这里,符合评价标准,即是符合良知的原则,从良知的道德义出发,我们或可说道德规范与道德原则是统一的。在生活实践过程中,心与物相接,认识不止,则评价不断。当生活境遇(人所面对的人、事、物)符合主体的价值标准时,主体就会对其作出肯定性的评价,并产生幸福感。从王阳明的心物之辨出发,这种肯定性的评价并不是对客观之物的评价,而是对意义世界中的物的评价,在实质上是对人之为人的确证,抑或说,是对良知的自信。正是基于良知自信,这种幸福感富有理性内涵,而表现出对感官快乐的摒弃。王阳明曾以“自慊”表示这种幸福感:“物无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无有亏缺障蔽,而得以极其至矣。夫然后吾心快然无复余憾而自慊矣。”[10](P1019-1020)为善去恶要即物而为,依良知而行。物与良知所发之意相接,物之“善”“恶”在于意之“善”“恶”,这就是对物的评价。善与恶都是良知之知者,即物而致知,最终是要达到良知的圆满自足,无有亏缺障蔽,这样才能自慊而无余憾。“物”在致良知功夫中为意之所在之物,即是心涵摄之物,所以,在阳明这里,格物即是格心,诚意即是诚心,最终都是要达到良知的自足,“只此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自慊,便是致知矣。”[11](P211)这种“自慊”也就是阳明所讲的“心之安处,即是良知。”依良知而行内心便快乐满足,违良知而行则感到不安。显然,“自慊”就是人对自已履行道德义务而产生的愉悦感和满足感。需要指出的是,阳明学的道德情感满足是建立在自觉与自愿基础上的,是依良知行,而非行良知。如阳明讲君子的境界:“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1](P79)君子在把握当然之则后,自觉地以此规范自己,进而达到“自慊”,体现了自觉原则与自愿原则的统一。自愿原则突出了主体的自主能动性,一切出于真心,随心而为,而皆能得自然之妙,又达到了陶冶和涵美内在精神的大功利目的。自觉原则则从理性上对这种行为给予规范,在外部不使其流于动物性和狂滥,在内部则使其行为动机(意念)本身就是出于理性的范导。[9](P130-131)可见,阳明学视域中的幸福感既有情感性,更有普遍理性,幸福感不仅是个体的追求,也同样是社会群体的共同取向。
人对幸福的追求存在于整个生活实践过程中,呈现为良知由本然状态走向显在状态,这其中包含着人性的发展、自身的完善和自我的实现。从阳明学的心物关系出发,这种自我实现过程即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过程,它不但肯定当下,也指向未来,这是由幸福的理性维度决定的。以良知为基础的幸福同时也内含着道德之维,这担保了幸福追求的正当性。基于此,人对幸福的追求是具有善的性质的,所以说,幸福中内含着道德规定,道德中内涵幸福诉求,人的完善与发展正是在道德规定与幸福诉求的统一中实现的。道德与幸福的关系正如良知的普遍性品格和个体性品格的关系,二者既有紧张,亦有统一。过多强调道德理性可能会一定程度上消解幸福感,过多强调幸福感则可能导向道德的抽象化,只有扬弃道德与幸福关系中的片面性,人才能沿着良知之路走向全面发展。这正是阳明学、乃至儒学对人的价值的终极关怀。
可见,良知在生活话语语境中往往呈现出明显的道德情感性,在生活实践中,内在理性的范导使这种道德情感面向表现为对当下的不断超越和对自我完善的追求,这使良知呈现出显著的信仰向度。
综上所论,王阳明良知图式的道德、价值和信仰三重向度及其相互关系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学义理体系和信仰体系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新诠释、新发展。王阳明心学演化发展的深层问题意识在于知识、道德与价值的割裂,而其贡献也正在于对三者关系的弥合,贯穿于其中的理性维度使道德向度得以特别的凸显。当代文化语境对阳明学的诠释提出了新的诉求,其发展了阳明学对知识和价值的对象性的消解,而强调以二重性的道德为基础,重新建构一种具有可理解性和公共性的价值,从而由个体领域走向公共领域。领域的拓展使道德和价值的主体由个体走向公共性的类群体,信仰也因此由个体体验性走向公共性,抑或说具有概念式的可描述性,而阳明良知思想的理性维度和道德向度正是其义理系统的根源。以道德为基础的理性化的本体性建构,使信仰不但具有了人文性,同时也具有了超越性,这正契合了当代文化避免拜物教和偶像崇拜的理性要求。因此,王阳明良知图式的三重向度诠释既是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体现,亦对当代文化建设有着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二.传习录中[M].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2]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一.传习录上[M].
[3]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二.十咏良知四首示诸生[M].
[4]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三.传习录下[M].
[5]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七.亲民堂记[M].
[6]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六.答友人[M].
[7]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二十九.贺监察御史姚应隆考绩推恩序[M].
[8][美]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9]陆永胜.王阳明美学思想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10]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二十六.大学问[M].
[11]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五.与王公弼[M].
Morality,Value and Belief
——three dimensions of Wang Yangming's conscience schema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ntext
LU Yongsheng
(School of Marxism,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Abstract:The new dimension interpretation of Wang Yangming's "conscience" though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value resour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the new era. Morality, value and belief are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Wang Yangming's conscience schema in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ntext, which are respectively presented in the academic, political and living discourse context and are interrelated, forming the internal recognition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angming studies Knowledge structure. The conscience of moral dimension as a kind of moral reason is the unity of ideal goodness and reality goodness, and also the confirmation of human nature, which contains the confirmation of value. The value attribute of conscience is based on the moral attribute,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good" and "evil" of moral dimension to "good", "bad" and "Yes (right)" and "no (wrong)" of value dimension. The belief dimension of conscience is based on the affirmation of human virtue and value, pursuing self realization beyond the level, and finding the intersection of moral satisfaction and value care, individual pursuit and social identity in "happiness". The new interpretation of conscience in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ntext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era.
Key words:Wang Yangming; conscience; morality; value; belief
|
 当前位置:首页 > 新知速递 > 新知速递
当前位置:首页 > 新知速递 > 新知速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