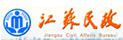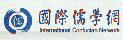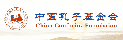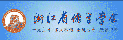|

【作者简介】 陆永胜(1978-),南京大学中国哲学博士,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阳明学诠释史研究”(17AZX006)
注:原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为方便阅读,已省略参考文献。若有转引,敬请注明。感谢作者授权于本公众号首发。
摘要:王阳明的经学观对其心学思想建构助益甚多,然研究甚少。王阳明的经学观在本质上是一个诠释学论题,在理论形态上呈现为显性和隐性双重结构:显性结构为由心体、以心释经的诠释进路与方法、明心立学的价值指向构成的系统化体系,隐性结构为阳明对知识、思想与价值关系的重新认识及三者的互动。其中亦包含不同于汉儒与宋儒的关于心与经、道与事、文与质等关系的新认识。阳明的经学观开启了明代经学思想史上的新篇章,对中晚明的学术、思想、文化具有重要影响,对多元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化建设亦有启示。
关键词:王阳明;经学观;以心释经;明心立学
当前的阳明心学研究成果更多地侧重于阳明心学之体系建构、思想内涵的多维阐发和学术地位与价值的研究,而较少从诠释进路和诠释价值指向的内在理论视角关注王阳明的经学观。这种研究趋向作为对心学思想的直接诠释本无可厚非,但犹如看到了心学之树的枝叶花果,乃至对花香与果实的想象,却忽视了培养心学之树的土壤——经学。依诠释学而言,王阳明的经学观是其心学思想之合理性、合法性建构的学术思想基础,因之与其心学体系密切相关。在宋明理学视阈内,阳明心学的建构语境是朱子学,故阳明学与朱子学的经学观既有承继融通,更有互质对立,这是阳明学在朱学语境中得以成功建构的保证。但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广阔视域看,经学诠释是汉以降学术思想的滋养,并不断推陈出新,同时,经学诠释的革新也意味着时代学术价值指向的变化。限于篇幅,本文所论侧重后者。
王阳明对“经”之价值的观点“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正可以描述阳明经学观研究的当下处境。目前虽有少数学者涉及此,探讨了阳明对“四书”“五经”的价值观、阳明释“经”的具体方法原则及其对经学发展的贡献,但似仍有对之做更为体系化、整体化、系统化研究的必要。笔者认为,王阳明的经学观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诠释学思想体系,其最为切要的核心包括两个层面:理论与逻辑的层面,即作为诠释进路和方法的“以心释经”;实践与价值的层面,即作为诠释价值指向的“明心立学”。这两个层面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具有内在逻辑的必然关联性。前者范导后者,具有从形上向形下转换的致用倾向,后者规定前者展开的可能限度、规范和领域,具有从形下向形上追溯理据的思辨倾向。同时,这两个层面还关涉不同的论域:“以心释经”的前提有两个:心体的确立和阳明对“心”与“经”的价值与地位判断;其展开则关涉具体的诠释方法与原则,这是担保和实现诠释进路导出诠释价值的关键。“明心立学”一方面和具体的诠释方法与原则直接相关,另一方面关涉阳明心学论述的重要论域:“心”与“学”。抑或可以说,阳明经学观的诠释价值指向在于重塑自身的学统观和道统观,也因此与当时的学统、道统及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生态密切相关。诠释价值指向与时代语境的关联性本身又构成了“以心释经”之前提和决定其进路选择的时代语境。可见,“以心释经”和“明心立学”作为王阳明经学观的核心理论抽象,其与时代语境的互动和二者间的逻辑辩证关系表明,阳明的经学观是一个圆融的、系统化的思想体系。
一、悟经立心与证经明心
正德三年(1508)春,王阳明于贵州“龙场悟道”,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象征性事件,“龙场悟道”既是一个历史事件,也是一个思想史事件,前者关涉史实,后者关涉意义。王阳明的经学观与前者相关,但更多地与后者相关,抑或说,“龙场悟道”奠基了王阳明经学思想的内在致思维度和价值目标指向。“龙场悟道”不应被看做是纯粹的瞬间顿悟的事件,从意义绵延的角度看,它包含体道、悟道和证道三个逻辑上可分的阶段,贯彻其中的两个关键词是“心”和“经”,包含“悟经立心”和“证经明心”两个方面。
王阳明初至龙场居于“玩易窝”,“阳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窝而读《易》其间。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无微,茫乎其无所指,孑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决,了兮其若彻,菹淤出焉,精华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优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内翕,视险若夷,而不知其夷之为厄也”。王阳明对《易》之体悟的情状于此有生动的描述。其实,王阳明在悟道前已有了生活、生命和道三个层面的体验,《易》对于阳明龙场顿悟心学之旨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特别是他对“体”“用”的认识:“体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动而化。神,故知周万物而无方;化,故范围天地而无迹。”“体”立而无所不知体现了“体”的主宰地位,“知”是体知,体现了“体”的主体性,因此,“体”具有本体-主体的双重性地位。“用”行而范围天地体现了实践的普遍性。天地万物是“体”之“用”的过化对象,在实践的过程中体用是合一的。抑或说,在王阳明看来,体不离用,用不离体,体用不二。而其更深层的具体内涵在于,“体”是用之行的依据,“用”是体之知的功夫与价值指向,“知”和“行”都具有本然层面的“本知”“当行”和实然层面的“体知”“实行”的意涵,并达到形上和形下的统一。王阳明对《易》的玩味体悟一方面在情感上疏通了其遭贬谪的抑郁之情,另一方面也使其原有的体验得到了升华,对其龙场顿悟“心即理”“知行合一”具有重要的激发作用。
据现有文献考证,阳明“悟道”当在“玩易窝”,“证道”的大部分时间在阳明洞。阳明面对种种生存窘况自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终于在一天夜里“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以一种神秘体验的方式悟得“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关涉“体立”,即对心体的确立,在内涵上体现为对本有之“心”的觉悟,将天理收归内心,即“心即理”命题的提出。这是阳明心学的理论基石,属于本体论的层面。“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关涉“用行”,即对功夫路径的调整和对价值主体的重新确立,在内涵上体现为对朱子学外求天理的功夫途径的否定,进而肯定了内求于心的心学功夫,此已涉及“知行合一”的功夫论层面。
《易》对“龙场悟道”的影响也同样体现在对阳明经学观的影响上。心体的确立是释经的出发点,价值主体的确立也同时规定了释经的诠释主体,内向性的功夫路径规定了释经的诠释进路。现有文献难以证明王阳明居“玩易窝”时还体悟了其它经典,但阳明悟道后的证道阶段则涉及“五经”。《五经臆说序》说:“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意有所得,辄为之训释。期有七月而《五经》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说》。”阳明高足钱德洪亦曾说:“师居龙场,学得所悟,证诸《五经》,觉先儒训释未尽,乃随所记忆,为之疏解。阅十有九月,《五经》略遍,命曰《臆说》。”可见,《五经臆说》是阳明证诸所悟的成果。
可见,阳明对《易》的体悟和心学的阐发是其经学思想和心学体系具有“天然”联系之根源。从内在致思向度看,如果说阳明心学理论是以“心”为逻辑起点的开放性阐发,那么,其经学思想则是从“心”出发对“经”的“逆向格义”,具有诠释理论指向的封闭性,这与朱子学经学思想的释经明理于心的致思向度是迥异的。从阳明心学体系的建构而言,如果说其心学理论是“经”,那么其经学思想则是“纬”,“经”“纬”不离,“纬”是阳明心学体系的建筑材料,其诠释价值指向是心学体系的建构(明心立学)。因此,从整个心学体系看,二者犹如“大厦”与“砖”的关系,但“砖”亦有其相对独立性和价值,是可以讨论的。无论是致思向度,还是诠释价值指向,阳明经学观都不同于朱子学经学观,阳明心学要在朱学语境中建构起来,其经学观必然表现为王阳明对朱子学经典观念的不同看法。此为一比较哲学论题,兹不赘述。
《五经臆说》原有《诗》《书》《易》《春秋》各十卷,《礼》六卷。阳明认为,“《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五经”内具圣人之学,其之于道,犹如筌之于鱼,糟粕之于醪。就筌与糟粕而言,五经更像糟粕,因为求鱼不能从筌上求,而求醪则可以从糟粕中得到。但对于求道之人来讲,目的在于道,而不在于讲读“五经”,得“道”则“五经”尽可去之。“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训释经典犹如渔人得鱼而忘筌,酿酒者得醪而糟粕弃之,所谓“鱼”“醪”即是“道”“心”,阳明证诸五经,即是要明心。阳明曾说:“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于此,我们可以看出,阳明把“心”的地位置于“经”之上,这和朱子学重“经”是不同的,而且阳明对“心”与“经”关系的认识自“悟道”后逐渐走向“学”的形态。
如果说“悟经立心”和“证经明心”是阳明“玩易”“龙场悟道”“证诸五经”等实践活动的总结,那么阳明“我注六经”的思想则达到了理论的自觉。在阳明看来,“《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故训释经典“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对于先贤,乃至孔子之言的判断取舍也须以符合“心”为标准:“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可见,以心为是,以经为“梯”是阳明经学观的重要内涵,其与宋代朱子理学“六经注我”的经学观有着鲜明不同,决定了阳明“以心释经”的诠释进路。从明代社会思想史的视域来看,阳明的经学观不仅仅关涉诠释进路问题,还关涉诠释价值指向问题。阳明从心出发重新检视《四书》《五经》和古圣先贤之言,既有倡复《大学》古本、阐发致良知说的“立学”价值,也有着以学用世的“经世”意义。
二、以心释经的进路选择与展开
明朝建业伊始,朱氏政权为了建构自身合法性与合理性,树立了朱子学为学术正统和官方统治思想,并不断对之进行制度化和俗世化建构,逐渐消解了其原有的超越性和开放性。经过太祖朱元璋的科举制度建设和成祖朱棣“三大全”(《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的编撰,在学术标准和政治标准的双重筛选下,朱学一方面“不仅成了有权力的知识话语,而且成了有知识的权力话语”,另一方面成为了科举之徒死记硬背的毫无生气、封闭、僵化的文本和交换权力的物品。在此学术背景下,“自贡举法行,学者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瞠然视,舌木强不能对。”士人思想僵化至此。当知识与思想被权力划定了边界,“朱学”作为对立物,一方面刺激了以维道为价值目标、以思想自由为标志的阳明心学的崛起,另一方面也促使新知识新思想探寻不同于“朱学”的生成进路。朱氏政权建构的官化朱学将外在之理和势绑定,形成服务于政权的“治道”。《四书》《五经》的训释也以服务“治道”为目标和标准。阳明心学即是在此思想、政治语境下以叛逆者的面貌出现的,它一方面否定了朱学的外在之理和官化的“治道”,确立了“心”的本体地位;另一方面从“心”出发重新检视经典,削弱官化朱学的经典依据,建构新的学说。由此可见,王阳明经学观“以心释经”诠释进路的选择有其时代政治、学术思想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阳明经学观“以心释经”的展开具有某种内在的层次性。首先,释经的认识论前提:“心”主“经”次。在经典与心体的关系上,阳明认为经典是指示心体的媒介,在价值上低于“心”。这种认识在某种意义上为他推崇古本《大学》、以“己意”训释“五经”提供了理论基础。在阳明经学观中,“心”重于“五经”,“五经”从属于“心”。人之为学在于明心,“五经”的作用就在于指示“心”。因此阳明说“《六经》原只是阶梯”,王阳明对于“心”和“经”关系的认识,显然也是基于其龙场悟得的心体。“五经”外在于心体,二者终有一隔,求“心”不能在文字间求索,而要做内向性的功夫。从功夫的角度言,心体具足还意味着功夫的起点、指向和目标皆为心体。这就为阳明以心释经的诠释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次,实求诸“心”,去除繁芜。既然经典对于心体具有指示作用,那么如果经典文辞繁复或过于驳杂,就不但不能很好地指示心体,而且还有可能遮蔽心体。因此,阳明主张治经要返朴还淳、化繁为简:
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阳明从“明道”的立场出发,认为道不明于天下,在于虚文胜而实行衰。因此主张返朴还淳,这也正是孔子删述“六经”的原因。例如《易》因《连山》、《归藏》之繁文而道大乱,孔子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尽废纷纭之说。其他如于《书》删《典》、《谟》以后之文;于《诗》删《九丘》、《八索》等文;于《礼》、《乐》尽废名物度数;于《春秋》则笔其旧,削其繁,目的皆在于删繁就简,返朴还淳,去其文以求其实。这种笃实的释经之风正是阳明所主张的,也体现了阳明关于文与质的思想。阳明认为繁文盛实行衰的原因在于学者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求知于世,是一种口耳之学,而非身心之学。这种注重影响的虚空学风使经学益乱,道益晦。所以为学释经就要反对这种“著述者”开启的学风,“敦本尚实”,“返朴还淳”。所谓“本”即是本心,所谓“实”即是实有诸己,返朴还淳即是要明心见道,突出经文之“质”。
再次,以“心”观事,道事圆融。从经典之“质”出发,阳明提出了“五经皆史”的观点,这和上述两点并不矛盾,也不意味着提高了五经之于“心”(道)的地位,而缘于论述角度不同。阳明在回答徐爱《五经》之事体时认为经、史、事、道原是一贯的: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庖羲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王阳明认为史与经的区别在于言事和言道的不同,从“言事”言,《春秋》为史,而且《易》是庖羲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从“言道”言,史亦可以存善恶,对于善者,可以存其迹以示法,对于恶者,可以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所以,道存于事中,事亦可以言道,如此事即道,道即事,“五经”亦史亦经,亦事亦道。所以,从经典诠释的角度看,需要从“心”出发,从“事”中体“道”。需要指出的是,阳明提出“五经皆史”说,其最基本的观点在于认为经书(事)承载着道,释经以明道(心)。
可见,阳明经学观“以心释经”的诠释进路选择自有其时代政治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宏阔背景,体现为学术思想演变中的革新与发展,同时也凸显出其在明代经学史中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在阳明经学观的体系内,“以心释经”始终与诠释价值指向密切相关,体现出手段与价值、途径与目标的辩证统一。
三、明心立学的价值指向
王阳明训释经典有着切实的价值指向:其一,从学术理论自身的创新发展而言,阳明通过训释经典论证良知心体的合法性、合理性,确立阳明心学的本体内核;其二,从社会思想史发展进程及其政治文化背景而言,阳明通过对经典的重新训释,另立学说,并争取道统的正当性。这两个层面的价值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融合的。
阳明经学观以心为主,去“文”求“质”的释经立场带来必然的诠释价值指向,即“明心”。从义理逻辑而言,阳明经学观呈现出心——经——心的诠释循环,“本然之心”经过“证诸经”而达到“明觉之心”,“明觉之心”成为再次释经的出发点,如此循环往复。在此意义上,以心释经既标示一种诠释进路,也是一种功夫方法,心体即在功夫中呈现。因此,在阳明看来,治经就是在做“明心”的致良知功夫:
《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
“六经”作为吾心之常道,其内容即是对吾心在天地自然、政务礼仪、性情诚伪等方面的表现的记录。所以,“六经”在本质上是心的记籍,求解“六经”不能从文义上求,而要从心体上求。君子与世儒之不同在于,世儒求“六经”之实于影响和文义,“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这样的治经之学造成的结果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而君子求“六经”之实于吾心,只有这样才能复明真正的“六经”之学:
圣贤垂训,固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一涉拘执比拟,则反为所缚。虽或特见妙诣,开发之益一时不无,而意必之见流注潜伏,盖有反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知觉者矣。
在阳明看来,虽然经典是圣人所作,但仍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地方,因此,看经书,最重要的在于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者,为我所用,而不能拘执于文字,或杂于意必之见,否则便遮蔽了良知。阳明的治经之学显然不同于汉学的考据训诂之习,同时也是对朱学“经所以载道”思想的发展。但阳明从良知出发,其治经的方法带来了不同于汉儒和朱学的两个变化:首先是把汉儒的经文为宗一变而为良知为宗,其次,把朱学视阈中经典所载之“理”(天理)一变而为“良知(心)”。所以,治经就是要明心体。在明代中期的学术背景下,其经学思想具有切实的实学价值。
如果说“明心”体现了阳明经学观的义理价值之实,那么,争取学术道统和官方认可则是其“立学”的社会价值的体现。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破”中有“立”,为“己说”建构经典依据。阳明从《大学》入手,主张《大学》古本,驳斥朱熹《大学》改本,从立论依据上驳斥朱学,彰显己说。
《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辞,既明白而可通,论其功夫,又易简而可入,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误?而遂改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
阳明认为《大学》古本为孔门相传之旧本,已相传千余年,不能轻易断定其有缺漏和错简,因此,朱熹对《大学》进行改正补缉,未必一定是对的。这是从《大学》古本流传的角度而言。另外,阳明以心之是非作为判断《大学》的标准。《大学》之学贵得之于心,只要得之于心而是,则出自谁的语言则无妨。其实,阳明是要暗示《大学》古本可以很好地表达心体,是没有错漏的,朱熹之改正补缉实属不必。“合之以敬而益缀,补之以传而益离。”这样阳明以“以心释经”的心学立场彻底否定了朱学立论的重要理据。
如果说阳明批评朱熹的《大学》改本属于“破”,那么他表彰《大学》古本,重建心学化的《大学》功夫,则属于“立”。阳明在《大学古本序》中表彰《大学》古本,并对《大学》功夫进行了心学化的阐释,从而使《大学》古本成为心学的重要经典依据。
《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则,致知而已矣。正心,复其体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谓之明德;以言乎人,谓之亲民;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体也。动而后有不善,而本体之知,未尝不知也。意者,其动也。物者,其事也。至其本体之知,而动无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则亦无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诚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实也。物格则知致意诚,而有以复其本体,是之谓止至善。
阳明认为《大学》功夫之要在于诚意,将诚意提到《大学》“八目”功夫之首,并以之将格物、致知、正心、修身一贯打通,以至善为心之本体和功夫的目标,从而使《大学》功夫具有向内求心体的心学化色彩。在具体功夫的内在关系上,阳明以“三纲”中止至善为本体,以内求诸己为明德,以推己及人为亲民。在“八目”则以致知为诚意之本,正心为复心体,以格物为致知之实功,修身为心体之用。同时以“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将“三纲八目”两个层次对应起来:诚意与止至善分别为“三纲”、“八目”功夫之首,且都是内外相合的功夫。明德为内求功夫,对应于致知和正心,亲民为心体之用,对应于格物和修身。内为体、为本,外为用、为末。由此,阳明建构了由内而外的功夫维度。这种功夫间的体用、本末关系与功夫维度和朱子学的重视向外格物,积理于心,以求豁然贯通的由外而内的功夫维度是截然不同的。阳明对《大学》功夫的心学化诠释使之成为良知说的重要经典依据。
第二,建构心学之源,跻身儒家道统。阳明通过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重新诠释,确立了心学之源,重新建构了心学道统,为其学说跻身正统做了理论和思想准备。
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谓也;道心精一之谓仁,所谓中也。孔孟之学,惟务求仁,盖精一之传也。而当时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贡致疑于多学而识,而以博施济众为仁。夫子告之以一贯,而教以能近取譬,盖使之求诸其心也。迨于孟氏之时,墨氏之言仁至于摩顶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内义外”之说,心学大坏。孟子辟义外之说,而曰:“仁,人心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盖王道息而伯术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济其私,而以欺于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无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谓天理者乎?自是而后,析心与理而为二,而精一之学亡。世儒之支离,外索于刑名器数之末,以求明其所谓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无假于外也。佛、老之空虚,遣弃其人伦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谓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遗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复追寻孔、颜之宗,而有“无极而太极”,“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之说;“动亦定,静亦定,无内外,无将迎”之论,庶几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后,有象山陆氏,虽其纯粹和平若不逮于二子,而简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传。其议论开阖,时有异者,乃其气质意见之殊,而要其学之必求诸心,则一而已。故吾尝断以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
朱熹吸收二程的“《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和“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的思想,曾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进行了阐发,从而确立了程朱理学的道统观,这种道统观将陆象山及其心学排除在儒学道统之外。王阳明则以“圣人之学,心学也”将儒学内在特质引向于“心”,并以“心”的角度重新审视理学道统。王阳明首先以三代相传之“十六字传心诀”为心学之源,然后以心法检视历代学术,由孔子而孟子而周、程二子,周、程之后而有象山陆氏直接孟氏之传。阳明心学道统与朱学道统皆以“十六字传心诀”为学术之源,但阳明以道心为心中之仁,从而使道心内具,实现由理学的外在之道向心学的内在心体的转化,成功把“十六字传心诀”改造为心学之源。在道统排序上不同于朱熹道统的最大之处在于周、程之后为陆象山心学,从而将心学列入儒家学术正统。阳明这里其实是在借象山为自己的心学学说正名和争取道统的合法性。事实上,阳明的这种努力在客观上达到了预期目的,无论是从反对心学的声音,还是官方的直接肯定,包括赐予其谥号、陪祀孔庙等事件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总之,阳明的经学观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它通过以心释经的方式既达到了发明本心,凸显“己说”的目的,也为学说建构了经典依据,追溯了思想源头,从内在本体和外在依据两个方面为其学说的确立解决了学统、道统等问题,从而使其学说得到广泛传播并得到官方的最终认可。
四、知识、思想与价值的检视
王阳明的经学观中包含着对知识、思想与价值的重新认识,并呈现了三者间的互动关系。从学术思想史的发展言,阳明认为“五经”之实具于“心”,把“心”置于“经”之上,这是与汉儒、宋儒不同的。阳明对“五经皆史”的心学化解读,也断裂了知识与价值的直接联系。在某种意义上,阳明经学观开创了中国经学史上的新篇章。从儒家诠释学的角度言,在阳明经学观中,“经”承载“道”,但不等于“道”,“经”不是主体,而是对象,“经”不能直接导致价值的生成。“心”具有本体-主体的双重性,它既是释经的主体,也是释经的出发点和目标。价值由“心”生成,也由“心”赋予意义。“心”是本有的,“经”是“心”借以建构价值的手段,作为目标的价值体现出“经”的价值指示作用。所以,阳明经学观呈现出“心”(思想)——“经”(知识)——价值(意义)的诠释图式,这与宋儒经学的“经”(知识)——“理”(思想)——价值的诠释图式是不同的。在某种意义上,阳明经学观是寓思想(“心”)于知识(“经”),然后由“心化之知识”导出价值,其诠释主体和价值基点是一致的,而朱子学经学观由格物(“经”)致“理”(思想),然后借由理“转出”价值,其诠释主体和价值基点是错位的。阳明经学观的诠释图式最终导致的是主观化的意义世界及其价值生成,而朱子学经学观的诠释图式则导致的是客观化的世界(从客观对象、客观之理到理化之价值)。因此,在宋明儒乐道的“尊德性”与“道问学”的表象下,二者存在着深刻的内在歧异。阳明经学观的独特之处也带来了中晚明儒学(心学)观念史的调整与变革,对当时及其后的学术、思想、文化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阳明的经学观有其局限性。第一,以心释经的诠释进路在某种程度上取消了“经”(知识)的独立性乃至正当性,当“经”(知识)成为思想和价值的附庸,其合理性与合法性便不再具有永恒性。第二,“心”的本体-主体地位使其既是诠释者,也是诠释的标准,当诠释原则缺失时,可能导致诠释的过度或随意化。阳明后学的衍化即是客观的证据。第三,价值作为诠释指向,其本身不具有实体性,而是需要在主观的意义建构和客观的时代语境(政治文化、学术思想等)共同作用下才能体现出来。脱离具体的语境,价值及其发挥将大打折扣。第四,从诠释理论而言,阳明的经学观有其理论的合理性与自洽性,其诠释方式和价值指向改变了以往的诠释思维模式,创造了心学学术思想的辉煌,但又在学术思想与时代社会的互动中趋于没落,其思想的开放性、义理的自我革新及适应社会变革的理论应对等值得进一步反思和研究。
在多元现代性语境中,阳明的经学观对现代社会的文化建设有多重启示价值。第一,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异域文化。文化思想与文化经典是文化传承的积淀,对之进行现代性诠释要做好保护、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以“己意”的过度或随意诠释是对文化的伤害,应注重诠释的时代有效性和合理性。第二,阳明以“心”为本的经学观具有强烈的伦理色彩,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也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需要。但阳明的“心(良知)”是具有超越性的,我们对现代社会现象的以“心”释之亦应有超越性,这样才能保证文化的普遍性和永恒性。第三,阳明的经学观是建立在以道统赓续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之上的,因此,“心(良知)”、经典、价值具有一致的内在属性和价值诉求。而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往往被不同政治、利益分割条块化,缺乏共同的文化基础。基于“心”的文化建设须以文化共同体的建设为前提,如此才能实现其价值导向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编辑:盛丽萍
审校:代玉民
|
 当前位置:首页 > 新知速递 > 新知速递
当前位置:首页 > 新知速递 > 新知速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