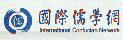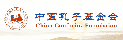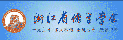|
作者简介丨马士彪(1991-),男,山东临清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助理研究员,主攻中国哲学。
原文载丨《中国哲学史》,2019年05期。
摘 要:当代主流的《老子》注解,往往把“明”诠释为一种理性的认识,但这种诠释脱离了《老子》文本的工夫论语境。老子之“明”所蕴含的工夫义、体验义与境界义,可以从冥契工夫、冥契体验和超转后的冥契生活三个方面得到有效诠释。透过“涤除”的否定性工夫,呈现出以虚静为体的“明”,是一种本体论的洞见,本质上则是一种“静态的智的直觉”。透过此直觉洞见,呈现由“自知之明”到“知常曰明”的冥契体验。在超转后新的生活模式中,“明”的本体论洞见转化为对于万物的平等性观照,此观照一方面体现为“微明”带出的“无为”,一方面体现为“袭明”带出的“无不为”;这种由平等性观照而来的生活模式,即物我冥合的玄同之境,落实了则是一种和谐的价值理序。老子“明”的冥契体验,表明了老子的道论实际上是一种境界形态的形上学。
关键词:老子;明;冥契体验;本体论的洞见;平等性的观照
本文所谓的“冥契”,有两种意义。一是传统的意义,指相合而无相合之迹。如李玄盛《述志赋》之“谅冥契而来同”《晋书·李玄盛传》、《关氏易传》之“灵应冥契”、《南华真经疏序》之“内外冥契”之类,皆为此意。另一是指与终极实在冥合为一。如牟宗三先生,在其著作中用“冥契”表述作为物自身的物,与本体协和为一而无相地呈现;杨儒宾先生则用“冥契主义”一词,对译英文的“mysticism”,而摒弃了“神秘主义”的旧译。他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中,“神秘主义”总是给人一种神秘兮兮的感觉,极易引发误解,所以主张用“冥契主义”取而代之,“冥”指“玄而合一”,“契”指“内外契合”,“冥契”两字合用,“取的是‘合’义。此种界定与冥契主义第一义‘内外契合,世界为一’,是相符合的”。
作为“东西方共通的哲学本体论基础”,冥契主义通常被定义为与位格神或无位格的终极实在合一的体验。威廉·詹姆士的《宗教经验之种种》,开启了对于冥契主义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按照彼得·穆尔在《冥契体验:冥契学说与冥契技巧》(Mystical Experience,Mystical Doctrine ,Mystical Technique)中的说法,从詹姆士(William James)、史泰司(Walter Stace)到福曼(Robert Forman),学者们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条路向,或者对于冥契体验的特征进行现象学的描述、对于冥契体验的类型加以总结;或者分析冥契经验生发出的各种哲学主张。罗浩(Harold D. Roth)在《原道:<内业>与道家冥契主义的基础》一书中将这两个路向总结为:冥契体验与冥契哲学。本文即在上述两层意义上使用“冥契”这个概念,而特别凸显主体与终极真实(道)冥合为一的冥契体验、冥契哲学以及在超转后的体道生活中主客合一的实践。
一种通行的做法是,把老子文本中的“明”解释为“明白”或者解释为一种理性的“认识和了解”,这种解释是把老子的“明”解释为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理性认知。但是,老子认为追求对规律把握的理性认知所代表的为学道路,是与为道相悖反的路向,而“知常曰明”章明显是在讲一种体道的工夫,这种工夫恰恰要求的是消解掉成立知识的条件与要求,因而把“明”诠释为一种理性认知的活动,就脱离了老子这一章的工夫论语境,这种知识论的注释理路使得老子文本中占据半数以上的工夫论文本得不到有效的诠释。本文试图结合二十世纪以降对于冥契主义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成果,从冥契工夫、冥契体验和超转后的冥契生活三个方面揭示老子“明”的观念中所蕴含的工夫义、体验义与境界义。
一、用光复明与见小曰明:冥契的工夫进路
对于冥契主义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终极实在可以有不同的呈现,但是达到终极实在的路径却有着共同的特征,即透过否定的方法加以把握。史华慈指出:“昂德希尔(Underhill)斯退斯(Stace)琼斯(Jones)和肖伦(Scholem),以及研究印度思想的权威学者们,虽然研究领域各自不同,但人们能从他们的著述中发现相当共同的基础。在他们的所有著作中,都能发现某种不能按照人类语言范畴加以讨论的观点:它们或者关于实在的基础(ground of reality),或者关于实在的终极层面(ultimate aspect of reality),或者关于“非存在”(nonbeing)之域(很自然,当讨论不可言说的东西时,所有的暗喻也都是可疑的)。它是这样的一种实在或实在的方面:用人类语言来描述的一切决断(determinations)、关系和过程都是无效的。”而对于这种超言说的终极实在的把握,只能透过一种“否定的方法”(via negative),这种否定的方法类似于冯友兰先生所谓的“负的方法”,即通过指出终极实在不是什么加以认识。尤有进者,在泛神论或无神论的冥契主义学说中,更有一套旨在达至终极真实的修养工夫,这种修养工夫可以概括为一种否定的过程、澄汰的过程或者遗忘的过程。
对于冥契主义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所揭示的共同特征,同样适用于老子对于道以及体道工夫的描述。道作为具有常存性、先在性、独立性的终极实在,无形无象,无法用特定的概念加以言说。面对超言绝象的道,老子并没有保持沉默,而是不断地加以诉说,老子采用的即是否定性的表达方式,如“道可道,非常道”(一章)“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十四章)之类,即是典型的否定性言说,这种否定性的表达并不肯定道是什么,而是说道不是什么,对道一有肯定,接着就否定掉,从而呈现出道本身的不可言说性。显然无法言说的道不能诉诸概念的把握,而只能透过某种工夫加以体证,这种工夫同样是一种系统的否定、遗忘、净化的过程。这种否定的过程,在老子即称为“涤除”、“专气”,而“见小曰明”、“复归其明”则是对于这一“涤除”过程的肯定性表达。透过这一否定的过程,在回归生命本真状态的同时与道冥契为一。
作为有限的存在者,人的肉体感性生命有口腹之欲,心则有知的作用。“欲”与“知”都是以物为指向外求活动,感性生命需要得到滋养,要求实现“五色”“五味”“五音”“驰骋田猎”(十二章)等感官欲求的满足;而心的知的作用则要求成立知识,透过心知的攀援,了别现象在时空条件中的质、量、关系等相状;然而,追求欲望的满足往往导致“盲”“爽”“心发狂”(十二章)式的感性生命之沉沦;人生的有限性与知识的无限性之间的张力,注定了心知的求索活动是以“有涯随无涯”(《庄子·养生主》)的悲剧性过程。尤有进者,老子把浸淫于欲望和知见中的心称之为“常心”(四十九章),“常心”即《庄子》所谓的“成心”,此所谓“常”与“变”相对,乃恒常不变之义,“常心”即胶着僵化之心,而以知见和欲望为其根底,因为有知有欲,所以有“我”,在老子则称之为“有身”(十三章),有“我”,则一切造作有为皆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万有皆被我之“常心”所扭曲,而在“常心”的是非好恶中以扭曲的姿态呈现。因而,老子要求回到未被知见和欲望染污的“无常心”,此一过程是一个不断“涤除”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损”的过程,“损”的内容则是“知”和“欲”,“损”的方法则是“塞”与“闭”:
“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五十二章)
“门”即“天门开阖”的“天门”,高亨在《老子正诂》中引《荀子·天论》“耳目口鼻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馆”及《淮南子·主术》“目妄视则淫,耳妄听则惑,口妄言则乱,夫三关者不可不慎守也”,而断之谓“天同于《荀子》之天,门犹《淮南子》之关。盖耳为声之门,目为色之门,口为饮食言语之门,鼻为臭之门,而皆天所赋予,故谓之天门也。”“兑”,奚侗注:“《易·说卦》:‘兑为口。’引申凡有孔窍者皆可云兑。”依是,则“兑”与“门”两字,词异谊同,皆指耳目鼻口等生理感官,借以喻人的欲望。顺感官欲望的要求往前走,济事逐物,往往中风偏走,陷入“盲”“爽”“发狂”的境地,因而在消极的意义上,老子便主张摒除作为各种造作有为之内驱力的欲望,以回归无欲的素、朴状态。“塞兑”“闭门”则无欲,无欲则无事,因而可以收到“不勤”的效果,老子又把这种无欲的素朴状态称为“见小曰明”。“常无欲,可名为小”(三十四章),“小”即“无欲”,因此,“明”即指心剥落了欲望后的存在状态。
工夫的否定过程本身意味着对于日常生存状态的超越,而这一过程又往往意味着对于某种本真状态的复归,老子称回复这种本真状态的工夫为“专气致柔”(十章)。王注:“专,任也。”徐复观先生本此进一步推论说:“‘专气’,是专于听任气,气指的是纯生理的本能。‘专’是指无气以外的东西渗入,亦即无心知作用的渗入……这种纯生理的混浑态度,老子比之为婴儿、赤子、愚人。”释“专”为“任”可从,但是认为“气”指的是“纯生理的本能”则不妥。既言“比之”,则应当了解到老子只是在譬喻义上使用这些名词,因而不能对“婴儿”“赤子”作字面上的解读,但徐先生显然没有将两层意思区分开,而将譬喻义的无知无欲与字面义的纯任生理本能混为一谈,既而认为婴儿纯任生理本能的无知无欲,与体道者经过否定的工夫所达至的无知无欲状态是一回事。事实上,即便在儒家,纯生理的本能之气仍然是落在“愚”、“鲁”、“辟”、“喭”(见《论语·先进》篇)或者宋明儒家所说的气质之性上,因而不可能一往是“柔”的状态,生命仍有可能走作造为,盲、爽、发狂。
《老子》“专气”的“气”指的是更为本源的“冲气”,所以他说“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十章)又说“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又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五十五章)冲气之和正是“专气致柔”的作用,因而,此处所专之气自然是冲和之气,这是剥落了心知作用后的存在状态,老子又称为“用其光,复归其明”(五十二章),“光”在古代往往和知识连在一起,老子的用光复明,即收视反听,消解心知的作用,而反光内照,一归于心的冲和本明。
“涤除”、“专气”都是对体道工夫的否定性描述,这一工夫仍然有正面的肯定,老子称之为“玄览”。“玄览”即“明”的作用,人的心刊落了知的作用与欲望的要求,成为无任何杂染的纯白之域,恰如浊水,静止下来,渣滓自会沉淀下来,而水也回复它原始的澄明,此即所谓“浊以静之徐清”(十五章)。老子称净化后心的作用为“玄览”,“玄览”历来解释不一,高亨先生说:“‘览’读为‘鉴’,‘览’、‘鉴’古通用……玄者形而上也,鉴者镜也,玄鉴者,内心之光明,为形而上之镜,能照察事物,故谓之玄鉴。”,帛书的出土证明了高先生的说法。心的状态恰如一面镜子,欲望和知的作用正如镜子上的灰尘,拂去灰尘镜子自然恢复本然的明亮,可以照物,心剥落了知的作用与欲望,恢复到冲气之和的本然状态,亦能生出光明。尤有进者,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玄览”即“览玄”,“览玄”即观道,因而明的“形上之镜”不仅可以照物,而且可以观道。明是工夫所达至的一种效果、作用,主体在明的玄览中回复无知无欲的本真状态,从而与道冥合为一,因此,形式地说,“明”是一种把握道的智慧。
二、自知之明与知常曰明:冥契于道的内在体验
透过系统的否定工夫,回复心的内在冲和本明,冲和本明是一种把握道的智慧,这是从形式上对“明”做出的界定,对于“明”的内容意义无所诉说。总括地说,主体在明的玄览中与道冥合为一,“明”首先是对作为人的本真状态的虚静之德的把握,此为“自知之明”;“明”是虚静本心的寂照,这种寂照不仅可以照察本身之德,且万物也在“明”的寂照种回归本真的虚静之德,此为“知常之明”。从“自知之明”到“知常曰明”,个我真正实现了物我一如,天地万物在我的虚静寂照种一起呈现,由此可见,“明”是一种本体论的洞见,这种本体论的洞见,本质上是一种智的直觉。下面作分解性的陈述。
“涤除”的否定工夫在《老子》第十六章又被称为“致虚”、“守静”的过程: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涤除”是滤掉“知”和“欲”,专听任于冲和之气,从而回归道心澄明的本真状态。此净化后的道心,既不会向知的作用上倾斜,亦不会受欲望的牵引、扰动。不向知的作用上倾斜,则无“常心”,无“常心”则无“我”,无“我”则虚;不受欲望的扰动,则如水之无波,故是“静”。从性质方面说,“明”是一种以虚静为体的寂照,它一边照了,一边回复自己的虚静本性,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老子称之为“和其光”(五十六章)“光而不耀”(五十八章)“用光复明”。寂而常照,则寂非死寂,而有明照的作用;照而常寂,则虽有明照的作用,但却不会被物牵引、扰动,往而不返。所以明以虚、静为其性格,而虚、静的作用是“明”。
透过致虚、守静的工夫,个体自我剥落了知见和欲望,从欲望和知见所架构成的“情意我”(劳思光语)中超脱出来,回复无知、无欲的虚静本性,此即自我的真实本性,也即生命的本然常德。此需有进一步的说明,常德即与道冥合的德,老子又称为“玄德”“上德”“孔德”。“孔德”,王注:“孔,空也。”“孔”即“空”,“空”即“虚”,而“上德无为”(三十八章),无为则不烦扰,即为“静”,所以,虚静即人之常德。因此,明是虚静心的自然澄明,而此自然澄明又反过来照显自身的虚静本性,亦即照显自我之常德。
虚静本心的明觉寂照不仅照了自我之德,且能于万物纷纭中观照物的“归根”、“复命”。“根”即万物的存在的本真状态,“命”即其生之所以然,亦即其本真状态,因而“归根”与“复命”都是指某种本真的存在状态。在虚静心的明觉寂照中,物物各回归其虚静之本性。由于虚静的道心是净化之后的无知无欲的冲和状态,因此对于所照察的物,并不把它们放在时空的条件下加以认取,而是直接直观其本性,在这种直接的照察中,物得以回归其自身虚静的本真状态,即回归其本性之德,回归其生命之“常”,也即回归其本根之命。
如上所述,虚静的工夫,呈现出的以虚静为体的无常道心,并不是毫无生命力的虚无与冷寂,虚的涵容性恰恰可以涵容万有而浑同为一;静的无目的性,也可以应物而不伤,物即不会在常心中被扭曲,心也不会被物扰动而不安宁,此即“两不相伤,德交归焉”(六十章)。在虚静心的明觉寂照中我与物皆回归生命的本真之“常”。而“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十六章)王弼注:“无所不包通也,无所不包通,则乃至于荡然公平也。荡然公平,则乃至于无所不周普也。无所不周普,则乃至于同乎天也。与天合德,体道大通,则乃至于穷极于虚无也。穷极虚无,得道之常,则乃至于不穷极也。”王弼的注很能揭示出明的寂照所带出的冥契体验,在虚静心的明觉寂照中,物、我之本性协同朗现,亦即协同回归虚静的常德,所谓的“容”,即万物在体道者道心的寂照中呈现虚静本性,我的虚静本性即玄通于物的虚静本性,因而我之虚静本性即包通物的虚静本性,以两者本来无二故;我之虚静本心洞见我之本性与物之本性本来无二,因而可以平等地对待天地万物,而肯定其呈现出来的差异性,此所谓“公”。王弼读“王”为“往”,道心的明照呈现出物我的本性本来无二,因而我之本性即物之本性,洞明我之本性即洞明物之本性,因而我之虚静本性即遍在于天地万物,此即所谓“普”;无不周普,恰如天之无物不覆,又如天之虚静,无形无象而无限,此所谓“天”;与天合德,无不包通,玄通万物,则与道同体,此所谓“道”,这样,透过虚静心的明觉寂照洞见物我之玄德,既而透过玄德回归于道。
透过道心明觉的寂照,洞见物我的本性,从而玄通物我,冥合于道,“明”即是一种“本体论的洞见”(ontological insight)。把“明”规定为一种本体论的洞见,仍嫌笼统,因此,仍需就“明”的本体论洞见所得以成立的条件作分解性的说明。
明作为虚静心的寂照,并不把一物推出去,放在时空的条件中加以认识,即并不成立追求因果性的知识性活动。在虚静心的寂照中,主体把自己从时空相中脱离出来,客体也从时空相中脱离出来,而与主体一同呈现其虚静本性,在这一呈现中主客冥合无间。我们很容易把这种不假借任何感觉印象与知性范畴中介的观照与伯格森所说的“直觉”联系起来。伯格森在《形而上学导言》中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一种方法“迂回于对象的外围”,对于对象的认识取决于“我们所处的观察点以及我们用以表达自身的符号”;另一种方法则“进入对象的内部”,这种方法“既不决定于某一观察点,也不依赖于任何符号”。第一种方法是理性的分析方法,借助于概念的中介,对于事物作出静止的分析;而第二种方法则是直觉的方法,它直接进入事物内部,不依赖任何概念的中介而把握流动事物的本性。老子虚静心的明觉寂照同样是不依赖任何概念的中介,而直接把握“芸芸”兴作中万物的本性。但是直觉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事物的内部,我们从伯格森笼统的论述中并没有找到结论。
徐复观先生认为老庄的“明”是一种“孤立化的知觉”,这种孤立化的知觉,渗透着艺术的共感与想象,所成立的是一种美的观照,此在庄子即曰“物化”,在“物化”后前后际断的知觉中,与所观照的对象冥合为一,并在对象自身发现“第二新的事物”,因而他认为这种艺术的观照之超越,乃是“即自的超越”,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超越。但是老子虚静心的明觉是有着形上性格的“本体论洞见”,这种“本体论的洞见”诚然可以引发某种艺术的观照,但那已经是落在第二义上了,因而徐先生以艺术的共感和想象描述“明”进入事物内部的方式,对于“明”的形上性格无所诉说。
老子的虚静心所生发的明觉寂照,是一种能够洞见万物本性的形上洞见,在这种形上洞见中,我与物的虚静本性一同呈现,而我与物皆回归本真的存在状态。对于这种形上洞见,牟宗三先生的道心圆照型的智的直觉似乎更有解释效力。万物各归根、复命,即是万物在道心明照的智的直觉中复归各在其自己的状态,牟宗三先生说:“‘万物并作’是有。顺其‘并作’而牵引下去便是胶着之现象,此为现象的有。‘观复’即是不牵引下去,因而无执无着,故能明照万物之各在其自己也。”智的直觉单凭自身的活动就能给出它的对象,当透过“涤除”的否定工夫呈现道心的虚静明觉时,它即直觉自身为一在其自己,此即道心的虚静本性,此一虚静本性剥落了心知的作用与欲望的作用,因而它只是一个虚静的如如呈现,这种道心明觉的寂照不会对物进行理智的分析,也不会把物当做有待利用的工具,因而在这种明觉寂照中,物也得以恢复其本真的虚静,这一虚静是由道心的寂照活动所带出的,因而虽说万物在道心的寂照中亦如如的呈现而回归其虚静本性,实际上只是净化了的虚静本心对于万物的不干扰,因而所谓进入事物内部发现其本性的直觉,在这里,只是以不进的方式进入罢了。这样“物物之在其自己实非一对象,只是一理境”,因而道心明觉之寂照,就其真实的内容意义说,只是一种“静态的智的直觉”。
三、袭明与微明:冥契超转后的体道生活
以“涤除”的否定性工夫,呈现出以虚静为体的“无常心”,从而复归生命的本真状态,这一过程本身即是超越日常的人类生存处境而进入到另一种存在境遇中。这一新的存在模式的开启,端赖一种新的观看世界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本身来自于净化后虚静心的平等性观照。超转后新的存在模式,在《老子》一书中有两个面向。一是“无执”“无为”,此即体道者的“微明”;另一是“无不为”,此即体道者的“袭明”,这两个面向,看似相反,实则相成,老子总称之为“无为而无不为”。
在明的本体论洞见中,体道圣人与万物的虚静本性一起呈现,他体知到自己的虚静本性即是万物的虚静本性,此即所谓“知常容”,即在体知万物的归根、复命之常中,呈现出虚静无常心的涵容性,包通性,在这种涵容性、包通性中,体道圣人与万物冥合无间,如如呈现。因而老子形容达道者即谓其“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十五章),达道者的虚静本性即是万物的虚静本性,因而他体证到我之本性即通于物之本性,故为“玄通”;此种发自于我与万物共同本性的玄通不二,只出现于“知常曰明”的本体论洞见中,不可以耳闻、不可以目睹,因而是“微妙”、“不可识”;就虚静心的涵容性说,深弘能藏,涵容万物,故为“深”。此种对于万物固有虚静常性的体证,落实到具体的生活态度上,即是“微明”:
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三十六章)
释德清注:“此言物势之自然,而人不能察,教人当以柔弱自处也。天下之物,势极则反。譬夫日之将昃,必盛赫。月之将缺,必极盈。灯之将灭,必炽明。斯皆物势之自然也。故固张者,翕之象也。固强者,弱之萌也。固兴者,废之机也。固与者,夺之兆也。天时人事,物理自然。第人所遇而不测识,故曰微明。”老子此章言物势自然,丝毫没有权谋的成分在里面,当然有没有是一回事,后人将其解释为权谋之术则是另一回事,此处不论。虚静心的本体论洞见,洞见出天地万物共同的虚静本性,万物按照其本性自然的生发、条畅,或歙或张、或弱或强、或废或兴、或夺或与,或者彼此转化,都是顺其本性的自然变化,无需人力加诸其上,更不需要去有意把持,胶着于某种既成的状态,因而体道者只是端默无为,无为则无事,无事则天下自然清静。所以《老子》第二十九章总结到: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王弼注:“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物有往来而执之,故必失矣。凡此诸或,言物事逆顺反复,不施为执割也。圣人达自然之至,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乱而物性自得之也。”王弼此注,适可作“微明”章的确解,万物皆有其虚静常性,外在的施为造作,对于物之常性来说无疑是一种扭曲和伤害;物皆有变化往来,胶着某一暂时的状态,必然事与愿违。因而体道者只是守住自己的虚静本明,无知、无欲,不为、不执。
不执、无为只是对道心明照之本体论洞见的否定性描述,明的本体论洞见依然有其肯定性的效果,此即是“无不为”,老子又称之为“袭明”: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二十七章)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四十九章)
所谓的“袭明”,即超越了世俗以“常心”的区分、构画而来的善、恶区分,而在每一人、每一物身上,当下洞明其虚静的本然之性,亦即由虚静心的本体论洞见,照显其德,并进一步由此虚静常德发现万物各自存在的意义,此即所谓“德善”“德信”。所谓的“德善”与“德信”,即在明的平等观照中,照了万物的虚静本性,因而肯认每一人、每一物各自的本性并无不同;因而在每一人、每一物身上皆发现了其根源的价值。在明的平等性观照中,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体道者在明的平等性观照中只是呈现出物我之虚静本性,而并不加以区分,给出各种善或不善的名号,因而每一人在此一平等性的观照中皆不自以为不善,也不会自以为善,从而每一人、每一物皆在体道者的平等观照中回归自己的虚静本德中。此即圣人以不救为救的“善救人”、“善救物”。
“袭明”与“微明”的平等性观照的效果即“玄同”,即超越了一切的区别与对待,而与万物冥合无间。由对万物的本体论的洞见,照了万物的虚静本性,因而得以涵容万有,玄通物我,又因“玄通”而来的平等性观照,而在超转后的生活境遇中与物“玄同”,一体无隔。这种“玄同”的境界落实下来即是“和”,“和”是化差异、对立为统一的力量,在虚静心的平等性观照中,物我同归于虚静本性,因而各种现实存在的差异、矛盾与对立都消解在虚静明照的涵容性中,一虚静,一切虚静,万物并育而不害,此正是虚静心的平等性观照所带出的理想生存状态。这种状态老子又称之为“自然”,自然有两层涵义:顺其自然与自然而然。达道之士,在明的本体论洞见中,照了物我之虚静本性,因而无执、无为,顺物之自然;物亦顺其本性而而实现生命的自然条畅与无拘迫的舒展,从而实现自化、自正、自富、自朴,此即自然而然。
四、结束语
二十世纪以降的老学诠释,主流的方向是借助于西方的思辨形上学框架,将老子的“道”诠释为作为宇宙的本源和万物的本根的形上实体,从而将出一套道家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如胡适认为,老子的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冯友兰先生则认为老子的道为“万物所以生之总原理”;徐复观先生以老子的道为“创生宇宙万物的一种基本动力”,而劳思光先生以“道”为“经验世界恃之而形成之规律”。但是这种诠释理路,往往脱离了老子文本中的工夫论语境,因而,在这一诠释背景中,半数以上的老子文本得不到有效的诠释,而整个老子道家所呈现出来的,不过是一套并不成熟的宇宙发生论与本体论。因而在这样一种诠释风气中,老子的“明”被理解为一种理性的认识,也就不难理解了。
把“明”放入《老子》的文本脉络中加以考察,就不会忽略老子的“明”基本上都是在体道的工夫义、体验义与境界义的分际上立言这一事实,而把“明”按照认识论的框架,诠释为一种理性的认知与了解。老子的“明”,首先是透过一系列的否定的“涤除”工夫所达至的虚静心的寂照。在此一寂照中,洞见我与我之本性同为虚静,遂玄通物我,而与物冥合无间,而“明”也获得了一种本体论的性格,代表一种本体论的洞见,此一洞见乃以虚静为其根本性格,无知无欲,因而也无为无事,在此一平等性观照的自然之境中,物各付物,而各回归其本然状态,其结果则是万物自生、自长、自富、自朴的自然舒发。因此,“明”的体道境界中,道的性格只是虚静,体道的人生亦在于持守住此一虚静的作用。质言之,道的性格只是王弼注文所谓的“不禁”“不塞”,因而只是一种境界形态的存有。
老子的哲学,严格区分“为学”与“为道”两个路向,两者不可得兼,因而特别彰显一冲虚的境界,诚如徐复观先生所言,这种冲虚的境界乃是一种艺术的精神,下开中国的艺术实践。但是,仅仅持守此一高明的境界,并不能开出真正意义上的知性主体,而知性主体不能确立起来,科学就不会昌明。“为学”与“为道”不一定是水火不容的敌对关系,完全可以在开出知性主体的同时,保持冲虚境界的提撕作用,以使知性主体不会因为一意外求而中风偏走,盲、爽、发狂。
|
 当前位置:首页 > 新知速递 > 新知速递
当前位置:首页 > 新知速递 > 新知速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