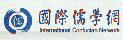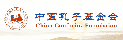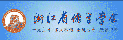|
作者简介丨王金凤,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原文载丨《哲学动态》,2020年09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摘 要:胡瑗的《周易口义》对“人事”具有强烈关注,而其典范意义具体表现为解释取向的预设性、体例形式的趋同性两个特点。《周易口义》因为具备“意义的有效”而得到宋代理学家的普遍接受和认同。与现代逻辑学“逻辑的有效”“实质的有效”“修辞的有效”等有效性评判不同,“意义的有效”能够为中国经典诠释的有效性判断提供更为适合的标准,也对以经典诠释为向度的当代儒学哲学化工作具有积极的启示。
关键词:意义的有效;人事;诠释有效性;经典诠释
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对易学发展脉络的总结——“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胡瑗的《周易口义》确实在易学史中具有典范意义。此前学界关于胡瑗思想的研究,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对胡瑗经学思想的研究,这类研究多数以《周易口义》为主体展开1;二是对胡瑗《中庸》诠释的研究,这类研究的文献基本来自《周易口义》涉及《中庸》的部分2;三是对胡瑗《周易》诠释的研究,这类研究集中讨论《周易口义》的创新之处及其哲学史意义3。以上述研究为基点,我们发现《周易口义》乃是胡瑗思想研究的重心。之所以如此,在于与之前的《周易》解释相比,胡瑗的《周易口义》存在着富有新意的解读。
然而关于《周易口义》的研究仍有值得深入的空间,这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带有递进关系的问题:第一,胡瑗《周易口义》与以往的《周易》解释有哪些区别?他的“新”体现出什么特点?第二,胡瑗《周易》诠释的“新”为什么被与他同时及此后儒者普遍接受?秉持“历史文化优先”意识的儒家群体,为什么能够接受和认同这种带有新意的解读?第三,胡瑗是如何做到这种“新”的?《周易口义》的新内容及其得到认同的原因,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有何意义?笔者认为,胡瑗《周易口义》与以往《周易》解释的本质区别,在于《周易口义》对“人事”的强烈关注,这又具体表现为解释取向的预设性、体例形式的趋同性两个特点。而《周易口义》具备的“意义的有效”,相比现代逻辑学以“逻辑的有效”“实质的有效”“修辞的有效”为标准的有效性评判,能够为中国经典诠释的有效性判断提供更为适合的标准。
一、什么是“新”:《周易口义》对“人事”的关注及其特点
《周易》是“占其筮辞”“为卜问休咎而作”4的周代筮书,与表征人类社会生活的“人事”存在先天关联。通过理解和把握“天道”来观照“人事”所代表的人类政治秩序与伦理生活,是《周易》的固有思想与核心内容。在易学诠释史上,虽然有象数与义理的分途,但其解释目标殊途同归——“推天道以明人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周易口义》延续了这个宗旨,胡瑗频繁地使用“以人事言之”这个语词,并且常与“以天道言之”的表述相对应。《周易口义》这种对“人事”的强烈关注,具体表现为解释取向的预设性与体例形式的趋同性两个特点。
1.解释取向的预设性
解释取向的预设性是指胡瑗《周易口义》明确表现出对“人事”的关注,并将此定性为一个预设的解释取向。那么,胡瑗“人事”的解释取向与以往诉诸“人事”的解释思路有什么不同呢?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放在易学诠释史的脉络中加以考察。在以往的《周易》解释中,“人事”是一种未被明言的内在理路;而在《周易口义》中,“人事”成为一个被反复提及和强调的核心字眼。通过比较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与胡瑗的《周易口义》,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样的区别。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卷首》中承接《易纬·乾凿度》对于“易一名而含三义”的说法,认为“简易、不易、变易”最终应当落在“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的意思上。其理据是“易者,象也”,而“象”取自“新新不停,生生相续”(《周易正义·序》)的天地万物及其运行规律。《周易》的写作目的正是使用万物变化之“象”进行有关人事的教化:“以作《易》者本为立教故也,非是空说易道,不关人事也。”(《周易正义》卷十一)但是,孔颖达没有继续阐述人事教化的具体内容与方式,而是直接引用了《易纬·乾凿度》“《易》者,所以断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的观点。至于对政治王道、人伦道理等“人事”的关切,则暗含在孔颖达的《周易》诠释中。
在胡瑗这里,“人事”成为一种预设的解释取向而被明确提出。在《周易口义》的开篇,胡瑗认同孔颖达“变易”的观点,但质疑“不易”和“简易”的说法:“于圣人之经,谬妄殆甚。……圣人作《易》,为万世之大法,岂复有二三之义乎?”(《周易口义·发题》)胡瑗认为,《周易》的创作初衷是通过“天道”更替说明“人事”变化,进而揭示“人事”的运作规律,因此,“以人事言之”就成为《周易》的创作初衷与终极目标:“大《易》之作,专取变易之义。盖变易之道,天人之理也。以天道言之,则阴阳变易而成万物,寒暑变易而成四时,日月变易而成昼夜;以人事言之,则得失变易而成吉凶,情伪变易而成利害,君子小人变易而成治乱。”(《周易口义·发题》)在对《周易》经传的诠释中,胡瑗细致地阐发了“变易”与“人事”之间的逻辑关系。首先,“变易”源于天地自然与人事的变化形态:“在《易》则为元亨利贞;在天则为春夏秋冬;在五常则为仁义礼智。”(《周易口义》卷一)其次,对应自然变化与天地之道,易学的旨归落实在“人事”上,即“圣人观天下之运动,明人事之得失”(《周易口义·系辞上》),“全以人事明其义也”(《周易口义》卷一)。通过这样递进式的论证,胡瑗指出爻、象变化的根源是人事关系的变化,而非象数派认为的卦气与天象的变化。比如,对于《复》卦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的解释,郑玄关注的重点是“七日来复”,并根据象数学的卦气说作出如下解释:“建戌之月以阳气既尽,建亥之月纯阴用事,至建子之月阳气始生,隔此纯阴一卦,卦主六日七分,举其成数言之而云‘七日来复’。”(《周易正义·序》)孔颖达接续了这种思路,不仅赞同《易纬》“六日七分之义”与王弼“阳气始《剥》尽,至来《复》时,凡七日”(《周易注·上经》)的解释,还对“七日来复”作出详细注解:“故离、坎、震、兑,各主其一方,其余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别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余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为八十分,五日分为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别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剥卦阳气之尽在于九月之末,十月当纯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尽,则复卦阳来,是从剥尽至阳气来复,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举成数言之,故辅嗣言‘凡七日’也。”(《周易正义》卷五)可见,以往注解没有给予“反复其道”足够关注,即便是孔颖达,也仅有“‘反复’者,则出入之义。反谓入而倒反,复谓既反之后复而向上也”(《周易正义》卷五)的解释。胡瑗则将理解的重点放在“反复其道”上,把与“人事”有关的伦理准则作为解释该卦辞的主旨,从而体现了“人事”解释取向的预设性:“‘反复其道’者,言阳气自上而反复于地,以生万物,皆得其道。犹君子之人,复于其位,进退皆合其道。‘七日来复’者,言阳气消。……圣人欲见其阳道来复之速,故以七日言之。”(《周易口义》卷五)
通过上述文献比较与分析可知,“人事”的解释取向是胡瑗《周易口义》的主导预设。因此,对“人事”的强调在其诠释中频繁出现。比如,对《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诠释,胡瑗的结论是“圣人备于《乾》之下,以极天地之道,而尽人事之理”(《周易口义》卷一);在对《否》卦上九爻辞《象传》“否终则倾,何可长也”的诠释中,胡瑗认为整个上九爻辞表达的是“劝之之意”,并给出了“此皆极言人事之道,而明《易》之深旨也”(《周易口义》卷三)的论断;胡瑗还在对《系辞》的解释中提出“大《易》之道,通于人事”(《周易口义·系辞上》)的观点。可见,胡瑗《周易口义》的预设和旨归是非常明确的,就是通过将《周易》的起源定义为一种经验的存在(“人事”),并设定为贯穿整个诠释过程的解释取向,从而使得《周易》的文本性质从卜问吉凶转化为对人类政治秩序与伦理生活的指导。
2.体例形式的趋同性
体例形式的趋同性指“人事”在《周易口义》中是作为一种固定的体例而普遍存在的。这种体例形式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存在固定的叙述形式,如在爻辞的解释中基本都会出现“以人事言之”的表达;二是具有趋同的意义指向,“人事”的意义被限定在政治层面的行事准则和伦理层面的指导上。胡瑗以前的《周易》解释,往往根据卦象、爻辞选择取象说、取义说、爻位说、互体说或卦变说等体例,而在胡瑗《周易口义》中,“以人事言之”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叙述形式,并呈现出政治、伦理的意义指向。
这种差异可以在王弼、孔颖达、李鼎祚与胡瑗对同一卦爻辞的不同理解中看到。比如,对《坤》卦初六爻辞“履霜,坚冰至”的理解,王弼《周易注》的体例主要是取义,具体思路是把六爻变化的状态看成对自然与人事变化的表现,从而根据爻变的情况说明卦爻辞的总体思想:“阴之为道,本于卑弱而后积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阳之为物,非基于始以至于著者也,故以出处明之,则以初为潜。”(《周易注·上经》)孔颖达《周易正义》则在取义的同时,兼顾取象说与爻位说等汉代易学体例,主张根据理解的需要进行“可以取象者则取象也,可以取人事者则取人事”(《周易正义》卷二)的选择。鉴于此,孔颖达从霜至冰的物象变化切入,引申出“渐渐积著”的含义,以表达“防渐虑微”的经验认识:“初六阴气之微,似若初寒之始,但履践其霜,微而积渐,故坚冰乃至。义取所谓阴道,初虽柔顺,渐渐积著,乃至坚刚。……不可不制其节度,故于履霜而逆以坚冰为戒,所以防渐虑微,慎终于始也。”(《周易正义》卷二)李鼎祚《周易集解》则多取卦气说与取象说,主要运用前人奇偶之数、卦变等象数学方法。他直接引用了干宝以象数解释《坤》卦初九爻辞的内容,指出“防祸之原,欲其先几”的人事含义:“阳数奇,阴数偶,是以乾用一也,坤用二也。阴气在初,五月之时,自姤来也。阴气始动乎三泉之下,言阴气之动矣,则必至于履霜,履霜则必至于坚冰,言有渐也。藏器于身,贵其俟时,故阳有潜龙,戒以勿用。防祸之原,欲其先几,故阴在三泉,而显以履也。”(《周易集解》卷二)相比之下,胡瑗的《周易口义》没有局限于取义说、取象说等体例,而是使用“以人事言之”的显性表达作为固定叙述形式,即根据“人事”包含的政治、伦理意义来选择取象、取义、卦气、爻位等体例。比如,对《坤》卦初六爻辞的解释,胡瑗先以汉易的卦气说与取象说阐发“履霜”与“坚冰”的意思:“夫坤之六爻皆阴,而初六居其最下,是阴气始凝之时也。大凡阴之为气,至柔至微,不可得而见,故自建午之月,则一阴之气始萌于地下,以至于秋,人但见其物之衰剥时之怆惨,且不知其阴之所由来。然于履霜之时,则是其迹已见,故可以推测其必至于坚冰也。”(《周易口义》卷一)再使用“以人事言之”的叙述形式,解释该爻辞的中心思想是“人君御臣之法”。对于这种“人君御臣之法”的具体论述,胡瑗采用的是王弼“本于卑弱而后积著”与孔颖达“渐渐积著”的解释,且在此基础上详细地说明了政治层面的秩序和准则:“以人事言之,则人君御臣之法……然为臣而佐君,必有行事之迹于其始,善善恶恶可得而度之,故在人君早见之也。见其人臣之间,始有能竭节报效,则知终必有黄裳之吉,乃任而用之,使之由小官至于大官,则为国家之福。若奸邪小人,其有谄佞之状,一露则知,积日累久,必至于龙战之时,故当早辨而黜退之,则其恶不能萌渐也。若使至于大位,以僭窃侵陵,则恶亦不易解矣。是由履霜之积,积而不已,终至坚冰,是宜辨之在始也。”(《周易口义》卷一)
不仅如此,对于先儒注解没有明确涉及“人事”的部分,胡瑗也常根据“以人事言之”的体例进行政治与伦理层面的阐发。比如,对《坎》卦《彖传》“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这句话,王弼的注解是根据物象说明《坎》卦“不失刚中”“不失其信”的性质:“言习坎者,习乎重险也。险峭之极,故水流而不能盈也。处至险而不失刚中,行险而不失其信者,习险之谓也。”(《周易注·上经》)孔颖达“今险难既重,是险之甚者,若不便习,不可济也,故注云‘习坎者,习重险也’……‘行险而不失其信’,谓行此至险,能守其刚中,不失其信也”(《周易正义》卷五)的疏解乃是对王弼注的扩充,并没有给出新的观点或理解角度。与王弼、孔颖达的注疏相比,胡瑗的解释充分体现了“人事”的叙述形式与意义指向。他将“重险”与“不失其信”的主语分别补充为“圣贤之人”与“君子之人”,具体阐述了圣贤与君子面对坎险所采取的行为,以此表现伦理层面的指导意味:“圣贤之人,欲致天下之事业,惟坎险之事最难,则必素习之,然后可以拯济其事也,故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者……犹君子之人,当险难之世,奋然不顾其身竭力尽,诚往而拯其难,无有凝滞,是犹水之流而不失其信也。”(《周易口义》卷五)
通过对上述易学诠释史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王弼、孔颖达等与胡瑗都是以“明人事”的思路理解《周易》,但胡瑗“以人事言之”的叙述形式更为固定与显性;在意义指向方面,胡瑗对政治层面的行事准则(君臣关系的处理)与伦理层面的行动指导(君子处世的方式)的呈现也十分突出。胡瑗《周易口义》对于“人事”的关注以及体例形式的趋同性直接影响了程颐《周易程氏传》,比如程颐也把《坤》卦初六爻辞理解为“圣人于阴之始生,以其将长,则为之戒。……犹小人始虽甚微,不可使长,长则至于盛也”(《周易程氏传》卷一),这与胡瑗“以人事言之,则人君御臣之法”的诠释基本一致。
二、“新”为什么被接受:对胡瑗《周易口义》的有效性考察
《周易口义》对“人事”的强烈关注及其解经特点,为胡瑗带有新意的解读提供了某种合法性论证。而这种新解读为什么能够被当时与此后的儒家群体认同与接受,以至于形成“从之游者常数百人”(《宋史·列传一百九十一》)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引入“有效性”这个概念来考察《周易口义》被认同与接受的原因。
“有效性”本是一个逻辑学概念,指评估论证的标准。学界对“有效性”有不同定义,具有代表性的是苏珊·哈克的界定:逻辑的有效(前提与结论之间存在适当联系);实质的有效(前提与结论都真);修辞的有效(论证能说服、吸引听众并使他们感兴趣)。5“有效性”这个概念在诠释学领域也有应用,如赫施认为“有效性验定的任务是去评价不同的解释体系”,并将“有效性”定义为“一种自我证实(self-confirmability)的解释”如何“令人信服”。6这实际上使用的是“修辞的有效”之意。根据上述说明,我们讨论胡瑗《周易口义》被认同与接受的原因,其实便是从“修辞的有效”来进一步引申讨论其诠释的有效性。
关于在“修辞的有效”(即如何吸引、说服他人)意义上谈论有效性,学者们通常认为被考察对象需要达到的标准之一是符合基本的逻辑理性、能够自圆其说。以此考察《周易口义》,胡瑗的解读在内容自洽或融贯方面其实并没有完全达到这一要求。《周易口义》最明显的问题是比附生硬和牵强附会,朱熹因此有“然窃尝读安定之书,考其所学,盖不出乎章句诵说之间,以近岁学者高明自得之论校之,其卑甚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薛士龙》)的感叹。比如,对于《剥》卦六五爻辞“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的解释,王弼与孔颖达都将“宫人”理解为“小人”:“若能施宠小人似宫人而已,不害于正,则所宠虽众,终无尤也”(《周易注·上经》),“宫人被宠,不害正事,则终无尤过”(《周易正义》卷四)。李鼎祚引用的是何妥的注解,认为“鱼”比喻“众阴之主”:“夫宫人者……各有次序,不相渎乱。此则贵贱有章,宠御有序。六五既为众阴之主,能有贯鱼之次第,故得‘无不利’以矣。”(《周易集解》卷五)胡瑗则进一步发挥了王弼与孔颖达的理解,认为“贯鱼”是形容“小人众多”,“无所不利”的结果来自“厚之田宅加之金帛”的笼络,这种强行比附的诠释带来理解上的生硬:“是小人之众,若贯鱼然也。……今六五当至尊之位,虽小人众多如贯鱼然,但厚之田宅加之金帛,而不使窃天下之权,如宠宫人而宠之,则无所不利也。”(《周易口义》卷五)
同样的问题在胡瑗对《解》卦九二爻辞“田获三狐”的解释中也有体现。孔颖达的疏解基本上照搬了王弼的解释,认为“田获三狐”说明的是“得乎理之中道”之意:“处于险中,知险之情,以斯解险,无险不济,能获隐伏……田而获三狐,得乎理中之道,不失枉正之实,能全其正者也。”(《周易正义》卷六)李鼎祚引用虞翻的卦变说,以“变之正”(《周易集解》卷八)说明“田获三狐”的含义。胡瑗没有采取上述任何一种解释思路,而是以“狐”比喻“民心”,“多疑”的性情比喻“民心尚疑”的状态,君子因此需要“使民心无所疑”,这样的诠释带有明显的附会意味:“‘狐’者,隐伏多疑之兽也;‘三’者,言其象也。蹇难初解,民心尚疑,犹恐未脱于难而又入于蹇,故君子当行其教化,革其残暴之政,易服色,改正朔,以新天下之耳目,使民心无所疑矣。”(《周易口义》卷七)
既然胡瑗的《周易口义》存在如此多问题,它为什么还能够吸引并说服众多学者,以至于形成欧阳修所说“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始来太学,学者自远而至,太学不能容,取旁官署以为学舍”(《欧阳修全集·胡先生墓表》)之情形呢?究其根源,《周易口义》的诠释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因为包含了以下内容而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
第一,胡瑗《周易口义》对当时思想家普遍关注或致力解决的问题予以了回答。土田健次郎指出,胡瑗“从《易经》经文中以类比的方式牵强地引出的人事话题,都是当时一般士大夫所关心的事”,因此《周易口义》的说服力“并不在于理论的逻辑性或考证的精确性,而大多在于其问题意识的时代性”7。可见,胡瑗的新解读之所以能够被儒家群体接受,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周易口义》的内容基本上是围绕政治与伦理两个主题进行的,而这正是当时思想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作为一种预设的解释取向和趋同的体例形式,“人事”在胡瑗《周易》诠释中的意义指向具体呈现为政治层面的行事准则与伦理层面的行动指导,表达出“明体达用”的现实诉求。比如,胡瑗通常对爻位关系予以政治化的解读:“九五”象征处于支配地位的“人君”,“六二”或“九三”则是“人臣”,六爻在卦象中所处的位置是政治关系与权力结构的体现。“夫一卦之中,凡有六爻,分其上下,有尊有卑有小有大。若九五则言君位,九三则言臣位,是尊卑大小各有其分,则贵贱之位从而定矣。”(《周易口义·系辞上》)因此,胡瑗将《履》卦九五爻辞“夬履,贞厉”解释为“以阳居阳,有刚明之德,而居尊位,为临制典礼之主”(《周易口义》卷三),并在此基础上阐发了“定典礼之是非,辨制度之中正,分上下之等夷,齐天下之民志”(《周易口义》卷三)的政治秩序。同样,对于《同人》卦《彖传》“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胡瑗以“既中且正又应于九五之尊,是得位得中而应乎乾也。以人事言之,则是有中正之臣而上应于乾刚之君。君臣之道同,则天下之人合心而归之矣”(《周易口义》卷三)的理解来诠释六二爻的意思。可见,《周易口义》在政治层面的诉求是通过讨论权力结构中的“德”“位”是否匹配问题,来表达一套关于制度化的行为准则与理想化的价值标准,并借此引申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等现实问题。
第二,胡瑗《周易口义》的言说方式或思维方式为当时的知识共同体所接受。依照“人事”之大义来理解经典文本的含义,是《周易口义》的言说方式与思维方式。“人事”所指代的常理甚至成为胡瑗判断《周易》经文是否存在增衍、脱漏的标准。比如,对《乾》卦《文言》中两句相同的“其唯圣人乎”,胡瑗认为按照“人事”的大义,“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可以合并在一起,因此第一句“其唯圣人乎”是多余的:“唯圣人为能知进而不忘退,知存而不忘亡,知得而不忘丧,故于衰耗之年,则求所代而终之,尧、舜、禹是也。上一句‘其唯圣人乎’,于义不安,当为羡文。”(《周易口义》卷一)同理,胡瑗认为《同人》卦《彖传》“同人曰”是后来添加的词语,其依据是“此三字盖羡文,于义无所通”(《周易口义》卷三);《贲》卦《彖传》脱漏“刚柔交错”,胡瑗的论据是“不成义理,当上有‘刚柔交错’四字,盖遗脱故也”(《周易口义》卷四);《大畜》卦上九爻辞“何天之衢”中的“何”字也是增衍,因为“推寻其义,殊无所适”(《周易口义》卷五)。这种诉诸“义”的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与汉唐儒者通过章句注疏来解经的方式存在明显不同,这正是与胡瑗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儒家群体所青睐的方式。范仲淹否定当时学者“刻辞镂意”“专事藻饰,破碎大雅”(《范文正集·尹师鲁河南集序》)的做法,主张“诸科墨义之外,更通经旨,不专辞藻,必明理道”(《范文正奏议·答手诏条陈十事》);孙复“病注说之乱六经”(《孙明复小集·寄范天章书二》),故其解经也是“出新意解《春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传十五卷》);欧阳修批评当时学者“不根经术,不本道理”(《欧阳修全集·论更改贡举事件札子》),提出“问以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欧阳修全集·详定贡举条状》)。可见,《周易口义》体现出的“以义理为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周易口义十二卷》)之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是当时儒学共同体的普遍趋向。
第三,胡瑗《周易口义》提出的价值取向或理论基型被儒学共同体所认同。胡瑗使用“人事”的解释取向与体例形式诠释《周易》,对其后的易学诠释影响甚深,理学家在他们的经典诠释中大都接续了这种切近人事的价值取向。比如欧阳修主张以“急于人事”(《欧阳修全集·易童子问》卷一)、“修身治人为急”(《欧阳修全集·答李诩第二书》)的讨论,取代以“穷性”与“天地鬼神之道”理解《周易》的做法:“夫专人事,则天地鬼神之道废;参焉,则人事惑。……推是而之焉,《易》之道尽矣”(《欧阳修全集·易或问》);张载认可《周易》占卜吉凶祸福的能力,但他认为这么做的前提是《周易》先验地包含了“人事”的全部道理:“《易》于人事终始悉备……《易》言天道,则于人事一滚论之”(《横渠易说·系辞下》);程颢也认为包含实践智慧的“开物成务”的优先级高于纯粹思辨的“穷神知化”,而“开物成务”就是“人事”的具体表述:“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徧,实则外于伦理;穷神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二程集·明道先生行状》);程颐尤其推崇《周易口义》:“若欲治《易》……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贯,余人《易》说,无取枉费功”(《二程集·与金堂谢君书》),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更有“予闻之胡翼之先生曰”“予闻之胡先生”(《周易程氏传》卷二)等表述,这种直接引用表明了程颐对《周易口义》的认同。
不仅如此,胡瑗通过《周易口义》所呈现的理论基型被儒者认为是“明体达用之学”,并成为南宋理学实践意识的学理源头。胡瑗对儒学经典文本的解释,不仅具备“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的理论面向,也包括“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宋元学案·安定学案》)的实践向度。其实,胡瑗本人在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很大程度来自其政治实践与道德践行的实用意识与现实展现。正如蔡襄“恳恳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后治乎人”(《端明集·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的评价,胡瑗《周易口义》提出了理学群体的一个核心论题:如何在纯粹形上思辨的道路之外,于日常伦理践履中寻找到实现道德自我与政治主体双重确立的方法。
三、如何做到“新”:“意义的有效”及其方法论意义
至此,我们需要回到一个基本问题上:如何理解“有效性”这个语词?通常认为,如果某种诠释与文本原意相符合,那么这种诠释就是正确的、有效的。可见,对于“诠释有效性”讨论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将“正确性”等同于“有效性”的预设,其理论基础是文本原意与诠释者理解之意的二分。因此,对于某种诠释是否“有效”的衡量,大都被转化为如下判断:诠释者理解的意思与文本原意是否相符。然而,随着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认知理论的推进,这种追求“客观性”“正确性”的诠释有效性遭遇了许多理论挑战。比如希拉里·普特南反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认为“一旦承认‘主观’和‘客观’的二分法,思想家们便开始将二分法的词汇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标签”8;威廉·詹姆斯也对我们惯常关于“正确性”的理解进行了反思,指出“‘真’只不过是有关我们思想的一种方便的方法,正如‘对’只不过是有关我们行为的一种方便的方法”9。同样,回归文本原意的可能性以及作者实在性的理论与实践,也遭到怀疑和解构,如海德格尔指出,“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理所当然的东西被先行给出的”的“先入之见”是不可避免的10;利奥塔尔也认为不存在一种“建立共识”的“具有真理价值的陈述”11;福柯更是从“作者是一个由于我们害怕意义增生而构想出来的意识形态形象”的层面,对“作者”的实在性与意义提出质疑12。可见,“逻辑的有效”“实质的有效”不能成为诠释有效性的唯一判定,“修辞的有效”为诠释有效性的判定提供了很好的补充。但是,“逻辑的有效”“实质的有效”可以通过经典逻辑的规则来判定,“修辞的有效”却很难找到相应的具体标准来进行判断。很多学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陈汉生就指出:“一个诠释就是一个理论。它像其他科学理论那样,我们对这个解释理论作出好坏的判断,是通过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诠释理论内部的数据信息。然而,判断这个解释理论是否‘最为符合’诠释理论内部的数据信息,却没有详尽的、明确的标准。”13因此,我们需要为“修辞的有效”提供相对明确、可靠的判定标准,并对一种诠释理论能够吸引、说服他人的原因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概括,这也是人文基础学科研究者或隐或显的期望与诉求。
胡瑗《周易口义》具有吸引力与说服力的原因,恰好能够为“修辞的有效”提供具体的判定标准:(1)它能够回答当时思想家普遍关注或致力解决的问题。余英时认为,北宋初期是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建立时期,也是当时知识共同体形成政治主体意识的阶段。14胡瑗借助《周易口义》进行政治治理与伦理行动的讨论,一方面表现出儒学对于政治伦理生活一以贯之的重视,另一方面体现了将儒学义理应用于政治生活与伦理生活的积极态度。可以说,胡瑗《周易口义》对“人事”的强烈关注,就是为了解决“儒门淡薄、收拾不住”(《扪虱新话·儒释迭为盛衰》)的现实困境,并回应当时儒学实现新的学理转化的迫切诉求。(2)《周易口义》的言说方式或思维方式能够被当时的知识共同体接受。根据蔡襄对胡瑗“解经至有要义。……为文章皆傅经义,必理胜”(《端明集·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的概括可知,依照“人事”的常理来理解经典文本的含义是胡瑗《周易口义》的言说方式与思维方式。这种概括性、体系化的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被与胡瑗同时的儒家群体所使用。以“自我为法”15解构汉唐注重章句注疏的言说方式与思维方式,是当时儒学知识群体的共同趋向。(3)胡瑗提出的价值取向或理论基型能够被知识共同体认同。朱熹认为胡瑗虽然“说经是甚有疏略处”,但仍具备“推明治道,直是凛凛然可畏”(《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注重心性义理的“内圣”与强调“推明治道”的“外王”是理学的核心问题,胡瑗《周易口义》表现出“明体达用”的价值取向与理论基型,被当时与后来的理学群体认同与吸收:在“达用”层面有“人事”的价值取向,在“明体”层面有可供后来理学借鉴的性情理论基型。比如,在对《文言》“利贞者,性情也”的诠释中,胡瑗对理学最为关注的性情理论给出了初步说明:将“性”界定为“天生之质,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无不备具”的“正性”,“情”则是一种“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之来,皆由物诱于外,则情见于内”的“邪情”。(《周易口义》卷一)基于这一设定,胡瑗谈到了其性情理论的主旨:“凡思虑之间,一有不善则能早辨之,使过恶不形于外,而复其性于善道”(《周易口义》卷五)。他还援引《中庸》“诚”的概念,将道德修养方法具体化为:“委曲之事发于至诚,则形于外而见著,见著则章明,章明则感动人心,人心感动则善者迁之、恶者改之,然后化其本性”(《周易口义》卷一)。从理学的发展史可以看到,《周易口义》提出的“明体达用”之价值取向与理论基型,是宋代理学性情理论、道德践行与政治实践的重要思想资源。
由此我们发现,以上三种判定诠释有效性的标准是对“修辞的有效”的进一步界定,因为它们相对完整地回答了如何为“吸引、说服他人”提供标准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符合以上三种标准的有效性称为“意义的有效”。因此,对胡瑗《周易口义》诠释有效性的考察就具备了普遍的方法论意义:某种以经典文本为载体的诠释行为要想具备诠释的有效性,就需要满足“意义的有效”。对于以经典为载体、以诠释为路径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建构来说,相对于现代逻辑学的有效性评判,“意义的有效”能够提供更为适合的标准,这也为以经典诠释为向度的当代儒学哲学化工作带来若干积极的启示。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面对的复杂境况,催生了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等认知范式,但这些认知范式皆不免会出现“伤害”传统哲学的情况。即使得到普遍认可的“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范畴、命题等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去理解”的自我认知范式,也存在“作为论证根据具有同一性、作为研究视野难免狭隘性、所获解释结论缺乏确定性以及价值诉求上的唯我性”等问题。16如何理解这些问题进而克服上述认知范式产生的诠释问题呢?笔者认为,其中关键在于处理好“如何借助经典文本的资源,建立一个能够对现代诸多哲学问题乃至社会问题予以回应的儒学新体系”这一问题。以胡瑗的《周易口义》为视角,笔者从中提炼出的“意义的有效”判定标准,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探索将中国传统资源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问题的路径,从而摆脱近代以来中西哲学“不平衡或不对称”17的关系。
注释
1参见何兆武:《宋代理学和宋初三先生》,《史学集刊》1989年第3期,第11—20页;张义生:《宋初三先生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2参见郭晓东:《宋儒〈中庸〉学之滥觞: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视角看胡瑗的〈中庸〉诠释》,《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27—32页;张培高:《论胡瑗对〈中庸〉的诠释》,《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1期,第50—56页。
3参见王新春:《胡瑗经学视域下的〈周易〉观》,《周易研究》2009年第6期,第3—11页;陈睿超:《胡瑗〈周易口义〉在释卦体例上的创新》,《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3期,第91—96页。
4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第10、56页。
5Cf.SusanHaack,PhilosophyofLogic,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p.11.
6Cf.E.D.Hirsch,ValidityinInterpretation,YaleUniversityPress,1967,pp.165-170.
7土田健次郎:《道学之形成》,朱刚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112页。
8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第1页。
9WilliamJames,TheMeaningofTruth,AsequeltoRagmatism,Longmans,GreenandCompany,1909,p.vii.
10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176页。
11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第2页。
12MichelFoucault,WhatIsanAuthor?IntheCriticalTradition:ClassicTextsandContemporaryTrends,DavidH.Richter(ed.),Bedford/StMartin's,2007,p.906.
13ChadHansen,LanguageandLogicinAncientChina,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83,p.6.
14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第8页。
15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第110页。
16参见李承贵:《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研究:探寻20世纪中国哲学复杂生成的一种视角》,《哲学动态》2015年第5期,第36—42页;《“自我认知范式”的形成、意义与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第33—43页。
17参见杨国荣:《超越非对称——中西哲学互动的历史走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39—44页。
|
 当前位置:首页 > 新知速递 > 新知速递
当前位置:首页 > 新知速递 > 新知速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