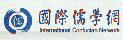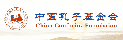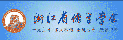|
李承贵
摘要:儒家认为,大凡生命所以成为生命,是因为生命物具有了成为生命的“所以然”,当这种“所以然”经由长期酝酿至成熟为生命时,生命宣告诞生。由于生命所以为生命乃其“所以然”的矛盾分化与互动使然,所以是“自生”,即“生命物自己生自己”。生命物自生过程中,必然衍生无数的有助于生命成长的生生行为,由于这些生生行为无论表现为怎样的形式,皆是源自生命内在的需求,所以也只能在“自生”范畴之内,此即所谓“全自生”。源自生命需求的“自生”行为复杂而多样,如积极有为的自生、消极无为的自生、不同阶段的自生、他力辅助的自生、无形无相的自生、冬藏之自生、自我认知之自生等。自生形式的多样性、普遍性,意味着“全自生”观念的客观性,亦意味着“全自生”观念内蕴了深厚的主体性,进而生发出如下意义:万物生生的本体形式是“自生”,从而建构起理解生生的体用模式;“自生”对于所有生命物而言是一种内在责任,没有任何推卸责任的空间;“自生”的成败乃生生自然,故不以誉喜,不以毁悲,忿怒作恶,全无用处;所有生命物的“自生”必须穷尽己之知识、体力、智能、德性等所有能量以赞助生生而无一丝遗漏,以使生生臻于完美。
关键词:儒家;全自生;意蕴
基于对儒家关于万物化生本根观念的考察和分析,笔者发现儒家所确定的“本体”,都具有自我否定特性而指向生命本身。诸如天地、太极、诚、气、道、理、性、仁、心等,都不是创生者,都不具有本体资格,而只能归于生命自身,即创生万物的根源是生命物自己,【1】也就是“自生”。万物自生,但生命物各有其性,因而自生的形式多样,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周易·彖传》)。自生形式的多样性常常引起人们对自生的误解,或者质疑某些自生不是自生,或者根本否定自生的存在。由于这些错误的认知,我们有必要发掘、凸显和确立儒家思想中的“全自生”概念。所谓“全自生”,是指与生命物关联着的所有生生行为,都源自生命物的内在需求,表现为原始性、自发性、自主性、自觉性等特点。以下考察儒家思想世界“全自生”观念的若干表现。
自生之“积极有为”形式。儒家自生理念首先需要妥善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定义生命物发出的“积极主动”的生生行为。这种看上去外于生命自身的积极有为的生生行为,诸如外于我的生生行为、群体的生生行为,是否属于自生? 人类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等方面的建设,属不属于自生行为? 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所有积极主动的生生行为,皆是出于生命物内在需要。也许这种需要的环节表现得错综复杂,但这并不能掩盖那些积极主动的生生行为是出于生命本身需要的事实。因此,生命物表现出来的积极的创造生命、养育生命、保护生命、成就生命等作为,不能因为是“积极主动的”,就被判定为“非自生”。事实上,这些行为是地地道道的“自生”。以三个案例说明之。一是自觉地结成组织以化解困境。荀子提出的“善群”行为,是因为“群生”出了问题,以致妨碍“群”生生,因而必须生生地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积极的作为,但这是基于“群生”的需要才出现的作为,并因此促使“群生”顺畅而富成效。荀子说:“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能以事亲谓之孝,能以事兄谓之弟,能以事上谓之顺,能以使下谓之君。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人结为群是为了更顺利地生生、更有成效地生生。“群生”出了问题,必须拿出办法,使“群生”和谐畅通,所以要“善群”。而“善群”必须隆礼义,“隆礼义”便是积极主动的行为。“隆礼义”是“群生”出了问题而表现出来的诉求,因而是“自生”。二是自觉地建构制度并惩罚恶行。朱熹通过对《尚书》中天叙、天秩、天命、天讨的解释,说明了这些“生生行为”皆是自生。朱熹说:“‘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若德之大者,则赏以服之大者;德之小者,则赏以服之小者;罪之大者,则罪以大底刑;罪之小者,则罪以小底刑,尽是‘天命’‘天讨’,圣人未尝加一毫私意于其间,只是奉行天法而已。‘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 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许多典礼,都是‘天叙’‘天秩’下了,圣人只是因而敕正之,因而用出去而已。凡其所谓冠、昏、丧、祭之礼,与夫典章制度、文物礼乐、车舆衣服,无一件是圣人自做底。都是天做下了,圣人只是依傍他天理行将去。如推个车子,本自转将去,我这里只是略扶助之而已。”【2】“天叙、天秩、天命、天讨”出自《尚书》:“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 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 政事懋哉懋哉!”(《尚书·皋陶谟》)所谓“天叙有典”,是说“天”制定了人间的人伦秩序,并要求人们遵守之;所谓“天秩有礼”,是说“天”制定了礼仪系统,并要求所有人遵循之;所谓“天命有德”,是说“天”任命有德之人,并制定了不同花色的礼服以表彰之;所谓“天讨有罪”,是说“天”惩罚有罪之人,并制定了墨、劓、剕、宫、大辟等五种不同的肉刑以惩罚之。无疑,“天”的这四种行为都属于生生行为。那么朱熹是怎样理解的呢?首先,朱熹将天命、天讨、天叙、天秩的内容具体化,并强调圣人未尝加一毫私意于这些行为中,只是行“天法”而已。朱熹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圣人所为,好比推车子,车子自转,圣人只是扶助而已。但显然,“天叙”“天秩”“天命”“天讨”并非“天”所为,而是内发于生命物对典章礼仪等制度的需求,以及对任命有德之人和惩罚有罪之人的诉求。朱熹有意强调圣人在这些行为中的“奉天法而行”,正是为了提示人们,借助“天”展开的积极的生生行为,也是“自生”。三是充分发挥生命的内在能量。王夫之在解释《易》之“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时说:“‘正大’,正其大也。此言人能正其大者,则可以见天地之情,而不为阴阳之变所惑也。天地之化,阴有时而乘权,阳有时而退听。而生者,天地之仁也;杀者, 物之量穷而自槁也。大体者,天地之灵也;小体者,物欲之交也。君子者,受命而以佑小人者也;小人者,违命以干君子者也。人唯不先立乎其大者,以奋兴而有为,则玩生杀之机,以食色为性,以一治一乱为数之自然,则阴干阳,欲戕理,浊溷清,而天地之情晦蒙而不著。唯君子积刚以固其德,而不懈于动,正其生理以止杀,正其大体以治小体,正君子之位以远小人,则二气絪缊不已,以阳动阴,生万物而正其性者,深体其至大至刚不容已之仁,而灼见之矣。”【3】这就是说,君子皆有“生理”“大体”“君子之位”,因而能以“生理”止杀、以“大体”治小体、以“君子之位”远小人,从而实现阴阳交合互动不已、化生万物并正其性。此即“正其大”。进言之,“正其大”即是要端正无私, 因为天地阴阳变化无常,复杂难测,无法捉摸,因而生生必然本能地预防、控制生生过程中出现的伤害生命之象;“正其大”就是发挥生命的主体性,以生命的全部潜能,“积刚固德”,坚持不懈,从而实现生生的畅通无碍。可见,王夫之对“正大”的解释显示的虽是主动的作为、积极的精神和蓬勃的气象,但却是生命内在需求的释放。因此,大凡积极作为者,不管形式如何多样,不管内容怎样复杂,都是自生。王夫之说:“生以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自取自用,则因乎习之所贯,为其情之所歆,于是而纯疵莫择也。”【4】就是说,生命积极主动的作为,虽然会出现取粹选疵之异,但都是生命物的自选自取。而且,取多、取纯、取驳,皆是生命的自我行为,王夫之说:“取之多,用之宏而壮;取之纯,用之粹而善;取之驳,用之杂而恶;不知其所自生而生。”【5】由于这些“积极作为”无不出自生命内在需求,因而不能因为积极努力而被视为“非自生”。进而言之,生命物所有积极有为的生生行为,诸如生儿育女、成家立业、修建道路、城市建设、耕地播种、求学谋职、工业生产等,无不是自生。但必须指出的是,自生行为并不意味着必然是对生生有利的,自生因为各种原因可能对生生产生伤害,但伤害性的自生仍然是自生,即只能按自生的要求和方式阻止或解决其中的“伤害”。
自生之“消极无为”形式。万物生生过程中,生命物之于生生,并非都表现为“积极有为”模式。生命物根据所遭遇的各种情形,会表现出不同的生生状态和方式。生命体遭遇困境时,需要用智慧来对待生生、疏通生生,有时需要消极无为地应对。由于这种消极无为的应对,也是出于生命物自身的需要,所以仍然属于自生。具体而言,生命物生生过程中,为了创造生命、养育生命、保护生命、成就生命,所采取的可能是比较消极的、迂回的态度和行为,但这种消极的、迂回的态度和行为对生生是有利的,只是出于生生的特殊需要而在策略上表现为“消极无为”。在浩瀚的“自生群”中,“消极无为”的自生形式不胜枚举。比如,董仲舒认为,君主治理或管理国家的方式应该是“消极无为”,但这个“消极无为”能够“乘备具之官、相者导进、摈者赞辞、群臣效当”,这就是“有为”了,而且是完美的有为。因此这种“无为”仍然是“自生”。董仲舒说:“故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无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足不自动,而相者导进,口不自言而摈者赞辞,心不自虑,而群臣效当,故莫见其为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6】人主或者国君,是生生而有,生生而有人、有伦理、有君主,因而人主是生生之自然;人主的产生是为了“治理”生生,因而人主当然有为。但人主的“治理”行为采取的是“任其自生”的方式,这种“任其自生”的方式不是消极无为,是“生生地有为”,也就是说,这种表面“无为”实际“有为”的方式是基于生生内在需要的,所谓“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因而当然属于“自生”范畴。再如,邵雍明确指出“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不固执地作为”,而且,不固执地作为才能广为,不固执地占有才能广有,为与有,乃生生之自然。邵雍说:“夫自然者,无为无有之谓也。无为者,非不为也,不固为者也,故能广。无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7】因此,无为、无有,皆生生自然。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不固执地为;无有不是真的没有,而是不固执地有。因而无为、无有不过是自然而然,也就是自生。无为、无有本质上是有为、有有,是自然而然地有为、有有。只有不刻意地有为,不刻意地有有,才是生生本有之态。既然能广、能有,那么“不固”之为与有,即是自生。因而“不固”并不是非自生,而是全自生。对儒家而言,无为,绝对不是无所不为,而是遵照自然规律地为,是讲究策略地为。“固”字,若与“故”同义,就是“故意地、有意地、自觉地、有主观意图地”,放在此句也可通,就是有意为之。非有意为之,反而能够广泛地“为”,不有意有之,反而能够更多地“有”。故是自生也。如果作“固执”义,那就是不固执地为、不固执地有,反而能广泛地为、更多地有。总之,邵雍用道家的命题表达了儒家的自生思想,即只有不违背自然规律地作为,才能更有作为、更多地拥有。再如,颜元认为,万物与我一体,我是“有作用之天地万物”,因而我的“作用”不外于天地万物。颜元说:“思天地一我也,我一天地也;万物一我也,我一万物也。既分形而为我,为天地万物之灵,则我为有作用之天地万物,非是天地万物外别有一我也。时而乘气之高,我宜效灵于全体;时而乘气之卑,我亦运灵于近肢。分形灵之丰啬! 乘气机之高卑,皆任乎此理之自然,此气之不得不然;不特我与万物不容强作于其间,亦非天地所能为也。”【8】既然“我的作用不外乎天地万物”,则天地万物与“我之作用”无分内外,从而拒绝“外力”参与其中,就算天地也无能为力,故为消极无为的“自生”。颜元以“万物一体”理论为依据,证成“消极无为”自生之形式的存在。总之,董仲舒、邵雍、颜元讲的“无为”,不是消极的无为,而是生生使然。生生过程中,有些问题只能采取“顺其性”的方式解决,也就是以“无为”的方式去应付效果更好,更有利于生生,因而这里的“不私”“不为”“我为有作用之天地万物”,都属于“消极无为”自生的形式,皆为生生之自生,当然不能被排除在自生之外。
自生之“不同阶段”形式。生命物的生生过程必然表现为不同阶段,生命物基于其不同阶段之需求而表现出的不同性质和方式的行为,也都是自生。生命物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创造生命、养育生命、保护生命、成就生命、尊重生命等行为,以及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生生的力量与方式的差异,都属于自生。不能因为少年时期的懵懂,就不属于自生;亦不能因为老年时期的孱弱,就不属于自生。就个体生命而言,其生命过程中势必要遭遇需要克服的各种困难与问题,只有采取措施进行自我养育、自我保护、自我成就、自我尊重,才能使生生通畅,所以不同阶段的生生都是自生。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这就是说,人生不同阶段必然出现需要解决的不同问题:年少时处于成长期,血气尚未成熟,因而不能为美色所诱惑而被伤害;壮年时,血气成熟旺盛,性情不稳定,因而需要克制,不能因为好胜争斗而被伤害;老年时,血气已经衰弱,必须懂得功成身退,不能因为倚老卖老而受伤害。质言之,如果生命物能够遵循此三个阶段的特性及规律,进行养育和保护,就能够顺利地成就生生。所谓少之时血气、壮年时血气、老年时血气,都是生生不同阶段之状况。由于这三个阶段的血气不同,所以需要做不同的养生、护生之事,因而都属于自生。程颐认为,人都好建立功名,这是生生之自然。建立功名是生生的内容,儒家生生理念肯定这一追求,但是,人的生命有盛有衰,这就会影响功名的多寡成败,因此,人建立功名的追求必然随着其生命状态的变化而调适。程颐说:“人之生也,小则好驰骋弋猎,大则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气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则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则有可怜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为形气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9】就是说,人的一生,一般性的兴趣或追求是骑马打猎,更为看重的兴趣或追求则是建立功名,都基于其血气之状况而然。如果血气衰弱,既无兴趣去骑马打猎,亦无兴趣于建立功名。所谓“血气”,是生命的基础,因而“血气”就是生命。既然驰骋弋猎、建立功名皆是“血气之盛”使然,这就意味着“驰骋弋猎、建立功名”皆是生命生长过程中的自然行为。血气而生命,建立功名亦是生生使然,但建立功名式的生生追求,受到基础生命的限制,因而这段话凸显了生生的层次性及其关系。生命不同阶段表现出的自我保护、自我养育、自我成就,出于生命本能,不能因为这些养生、护生、成生行为缘于迫不得已或刻意为之,就将其排斥在自生之外,它们也属于自生。生生必然是过程,生生的过程表现为不同阶段,不同阶段的生命需要养育、保护和成就,但都源自生命物的内在需求。而且,即便养生、护生、成生掺和了外在因素和条件,它们仍然是生命的自我行为,是自生。因此,不能因为是生命的不同阶段、不同状态,也不能因为生命不同阶段的自生资用了外在条件而否认其为自生;不能因为是生命不同状态表现出的养育、保护、成就行为,便不将其视为自生。生命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生的欲望,由此生的欲望而生发的“生生”行为,概为自生。
自生之“他力辅助”形式。生命物之生生,需要满足必要营养。有些营养是生命物通过自力更生而自我解决、自我满足的,有些营养则需要其他生命体的“支援”来实现,从而出现借助其他生命物以辅助生生的现象。那么,这种借助他力以助生生的行为,是不是自生呢? 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生命物借助他力,也出于自我生命的需要。哪怕是生命物借助神秘力量以创生、养生、护生,也是自生。儒家有“君为天命”的思想,即认为尘世间需要有人管理,因而必须树立君王。虽然君王由天或天帝派谴,但树立君王乃是生生的需要,君王之作为亦是生生的需要,皆生生自然者也,故是自生。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天立君王,非是来自生生之外,而是生生使然。就是说,人们为了纾困解难而提出宗教式要求,因此,天立君之类也是生生使然,并不是生生之外有一种神秘意志为天下人立君,所以,“全自生”亦包含了人类宗教式的需求与行为,但却不是神秘的,反而是对神学的否定。所立之君王,要为民众服务,乃是生生自然;如果君王不作为,不生生,或者生生出了问题,即自生出了问题,需要解决,则由生生解决。董仲舒说:“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10】刘基对“立君”之自生性质认识得非常准确且深刻,他说:“天生民,不能自治,于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杀之权,使之禁暴诛乱,抑顽恶而扶弱善也。”【11】民众不能自治,需要立君以治之。所谓“天生民”,是不存在的幻想;“民不能自治”在于生命自然欲望的膨胀所造成的冲突,这点“君”也不例外。因而“天立君”只是将生命物生生过程中的现象赋予神秘性而已。“立君”以禁暴乱、抑顽恶而扶弱善,乃是生命物生生之自然也,并非外于“生生”逻辑,所说明的仍然是“全自生”。生命物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借助外力,完全出于自身的需要,所以也是自生。诚如《周易》所谓:“‘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周易·系辞上》)此即说,天之所助,自生也;人之所助,亦自生也;但人之所助,乃自觉自生。不过,借助他力自生,必须与需要帮助的生命物特性相契,才能获得预期效果。戴震说:“气之自然潜运,飞潜动植皆同,此生生之机肖乎天地者也,而其本受之气,与所资以养者之气则不同。所资以养者之气,虽由外而入,大致以本受之气召之。”【12】既然借助他力以生生必须与所受助生命物特性相契,则说明借助他力以生生正是出于生命物内在需求,所以是自生。因此,借助他力辅助而生者都是自生。戴震说:“况气之流行既为生气,则生气之灵乃其主宰,如人之一身,心君乎耳目百体是也,岂待别求一物为阴阳五行之主宰、枢纽! 下而就男女万物言之,则阴阳五行乃其根底,乃其生生之本,亦岂待别求一物为之根底,而阴阳五行不足生生哉!”【13】气化生生,以阴阳五行为根底,无需在阴阳五行之外寻找主宰;男女万物生生,以阴阳五行为根底,亦无需在阴阳五行之外寻找主宰。故谓自生也。
自生之“无形无相”形式。生命物生生过程中,有时表现为无形无相、无声无臭,看不见,摸不着,但不能因为看不见、摸不着,就将其排斥在自我创生、自我养生、自我护生、自我成生之外。生命物潜移默化地自我创造、养育、保护、成就,亦是源于生生的自我需要,只不过这种形式比较神秘,不能为感官所感知。无形无相、无声无臭的生生行为,也是生生自然发出的,虽不轰轰烈烈,但润物无声。这里以三个案例考察之。首先,从生生之为道体看。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这句话通常被理解为:时间像流水一样不停地流逝,一去不复返,表达了孔子对人生世事瞬息万变的感叹,含有惜时之意。不过,如果依照程、朱解释为“道体”的运行不已【14】,那么可以说“川流不息”乃形容生命体处于生生不已之状,而且自生、自长、自转于无声无息、无形无相之中。杨简认为,“道”生万物是无形无相、无声无臭的。杨简说:“气虽即道,人惟知气而不知道;形虽即道,人惟睹形而不睹道;事虽即道,人惟见事而不见道。圣人于是乎不得不推穷其始而有元之名,且天行之所以刚健运化而无息者,其行其化何从而始乎,始吾不得而知也,始吾不得而思也,无声无臭、不识不知、无思无为,我自有之。”【15】由于“道”生万物于无形无相、无声无臭之中,无始无终,神秘莫测,人们只看到有形之物,不能看到无形之“道”,不能看到万物“生生”之本我,故为自生之“无形无相”形式。其次,从物为生生主体看。《易传》将万物化生之状描述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周易·系辞上》)万物生生,范围天地所有变化,成就万物没有遗漏,却“惚兮恍兮”,神不知,鬼不觉,看不见,摸不着,故为“无形无相”之自生也。荀子的描述更为生动亲切:“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荀子·天论》)万物生长于大自然,各得其和,各得其养,虽不见其事、不见其功,不能感知,却生生不已。万物自我生长、自我成就,是在“不见其事、不见其功”的情境下实现的,其和其养,荀子形容为“神”,但仍然内在于生命物本身。柳宗元认为,宇宙万物无时不在自生、自长、自灭、自转,而且都是“孤独地”完成的。柳宗元说:“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 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16】就是说,高山大河不过是天地间自然之物,阴气阳气不过是天地间的元气,它们自己运行、自己休止、自己屹立、自己流动,谁同它们商量过呢? 它们的冲突,它们的枯竭,它们的崩塌,它们的缺损,又有谁替它们安排过呢? 既然万物化生皆由自我做主,并不需要与人商量,并不需要他人安排,所以是“无形无相”之自生。最后,从礼乐辅相生生看。儒家制定“礼”,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以抑制祸乱的发生,是生命物主动积极的生生行为,但“礼”之养生、护生、成生的方式却是无形无相、无声无息的,表现出神秘色彩。《礼记》说:“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礼记·经解》)“礼”生于禁乱,即谓“礼”的产生源于祸乱,而祸乱是生生过程中的祸乱,即生生出了问题,所以需要生生解决。因此,生生过程中建立“礼”是自生的行为,源于生生出了问题所提出的需求。来自生生需求的“礼”,当然要解决问题———“乱”。“乱”得到了理顺,生生回归正常,如婚姻礼、乡饮礼、丧祭礼、聘觐礼等。但“礼”养生、护生、成生的方式是无声无息的,所谓“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虽然微而不见、止而未形,但却是源于生生的自生行为。与“礼”相比,“乐”之为生生“无形无相”形式更为典型。“乐”可以调节不同生命物的身心,以使其和生共长。荀子说:“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荀子·乐论》)此即说,“乐”的推行,可使君臣上下和敬、父子兄弟和亲、老少妇幼和顺,从而使整个社会和和美美,因此,“乐”乃“审一以定和者”。对个体生命而言,“乐”也具有安顺、长久之功,《礼记》云:“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礼记·乐记》)这就是说,人若沐浴在乐教之中,便能产生平易、正直、慈爱、诚信之心,从而使生命安顿、安顺、持续、永恒。故此,推行“乐”的教化,不仅可以美善人心,而且可以纯化风俗。荀子说:“乐者,圣王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荀子·乐论》)总之,“乐”之于生生而言,具有滋养、培育、纯化的功用:“乐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礼记·乐记》)“乐”生于“心”,也就是出于生命的内在需求,所以,“乐”的教化、滋润虽然悄无声息,但也是自生。
自生之“冬藏”形式。生命物的生生过程,依《周易》元、亨、利、贞“四德”,“贞”是“藏”,即生生过程中会出现“藏”环节,虽然与元、亨、利相比,“藏”显得内敛、低调,不张扬,但这个“藏”环节也属于自生。“冬藏”,此乃根据中国古代气象、农业知识形成的一种认知,即认为一年只有春播、夏长、秋收属于生生,从而将生生限制在春、夏、秋三季,冬季属于储藏,被排除在生生之外。但儒家认为“藏”也属于生生,而且是生生不可或缺的环节。《易传》曰:“‘乾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周易·文言》) 巨龙潜伏水中,暂不施展才用;巨龙出现田间,天下文采灿烂。所谓“阳气”潜藏,就是指生命养育生气,伺机待发。因而这个“藏”字是生命的自养、自护、自存,以待发用。董仲舒说:“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17】万物有生有杀,“藏”乃物生长之自然。至宋明理学,“藏”的生生意蕴才被全面、深刻地发掘、认识、肯定、凸显。朱熹说:“天只是一元之气。春生时,全见是生;到夏长时,也只是这底;到秋来成遂,也只是这底;到冬天藏敛,也只是这底。”(《朱子语类》卷六,载《朱子全书》第14册,第247页)这就是说,一元之气贯穿春夏秋冬,所以春、夏、秋、冬皆为生生环节。朱熹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虽分四时,然生意未尝不贯;纵雪霜之惨,亦是生意。”(《朱子语类》卷六,载《朱子全书》第14册,第256页)而“冬藏”虽然在形式上不表现为生生,其内容却是生生不可或缺的,故所谓“纵雪霜之惨”,亦是生生。在朱熹看来,春、夏、秋、冬皆是生生的必要环节,每个环节都是“生”,不能因为“冬藏”就否定其生生的意义,更何况“冬藏”是“生之成”。朱熹举例说,生命成熟七八分,如果切断它的根,就会丧失生命;如果没有切断,便可使生命完全成熟,则不会丧失生命。如此收而藏之,生似乎停止了,但来年播种,必然复生。朱熹说:“且如春之生物也,至于夏之长,则是生者长;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谷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斩断其根,则生者丧矣,其谷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丧,须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种之,又复有生。”(《朱子语类》卷二十,载《朱子全书》第14册,第696页)由此看来,朱熹将“藏”视为生命的完整之不可缺者,不完整而残缺的不叫“藏”,而且,生命的完整储藏了生命的种子信息,条件允许,来年再生,循环往复。因此,“藏”当然是自生。朱熹继续说:“冬,终也。终,藏也。生气到此都终藏了,然那生底气早是在里面发动了,可以见生气之不息也,所以说‘复见天地之心’也。”(《朱子语类》卷五十三,载《朱子全书》第15册,第1756页)就是说,虽然生命之生气到“冬藏”便意味着“终藏”,但生生之气早就蕴涵在“冬藏”里面发动了,所以是“生气不息”。这样,朱熹就将“冬藏”之生生义阐述得透彻而明晰。王夫之对生生过程中诸环节的特殊价值也有深刻的认知。他认为,生生有长、养、收、藏等不同阶段或环节,而“藏”是生生过程的自生。他说:“天之于物,有长、有养,有收、有藏,有利用、有厚生、有正德;而既不可名之曰长物之天,养物之天,收藏夫物之天,利物用、厚物生、正物德之天,如天子之富,固不可以多金粟、多泉货言之,则尧之不可以一德称者,亦如此矣。且天之所以长养、收藏乎物,利物用、厚物生、正物德者,未尝取此物而长养收藏、利厚而正之,旋复取彼物长养收藏、利厚而正之,故物受功于不可见,而不能就所施受相知之垠鄂以为之名。”【18】在王夫之看来,天“生”万物虽然分长、养、收、藏等环节,但都是生命“生生”的必要形式或环节,而且,万物自生,因而并不以长、养、收、藏谋名,只是自生而已,故“藏”亦生生也。总之,生生过程、环节非常复杂,“藏”看不见摸不着,却是默默地持续积蓄动能、孕育生机的“生”,因而谓之“冬藏”之自生。
自生之“自我认知”形式。儒家思想的特质之一,就是非常重视自我认识、自我反省,将自我认识、自我反省视为规范、提升自我生命的前提。由于这种自我认知源自生命的自我调适、自我完善需求,所以也属于自生。以下从三个方面考察。首先,从反省不足以完善自我看。生生过程是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而生生自我完善的前提之一,就是对自我的不足有清晰且准确的认知。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就是说,如果发现优秀品德之人,就应该向他学习,努力接近他;如果发现品德败坏之人,也必须自我反省,检讨自己存不存在类似问题,以便改正完善自我生命。这种自我反省以求完善自我生命的行为,完全出自生命的内在需要,所以是自生。孔子的学生曾子将生命的自知、自省视为基本习性,曾子说“吾日三省乎吾身”(《论语·学而》),强调自我反省对生命的重要意义。因此,如果爱人、治人、礼人等作为效果不好,就必须自我反省,找出问题所在,从而改正错误、完善自我生命。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王阳明认为,为学的主要功能就是反省自己,如果凡事责备他人,而不检讨自己,就不能发现自己的缺陷,也就找不到完善自己的切入点。他说:“学须反己。若徒责人,只见人不是,不见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见自己有许多未尽处,奚暇责人?”【19】因此,如果人欲显豁美德,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人是无能为力的。王阳明说:“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无所与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20】其次,从穷知自性以参赞万物看。生命的生生过程需要不断补充能量,而补充能量的前提之一,是生命物通过对万物特性的把握以顺利获取自己所需资源。孟子认为,全面、准确地认识生命本性,有助于准确地把握生命运行状况和规律,从而有助于自我生命的挺立和发展。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中庸》则认为生命的自我认知,有助于万物顺利地生生化育,《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就是说,生命至真至诚,才能无保留地认识、发挥其性能,也才能无保留地认识、发掘其他生命的性能,从而按照生命规律生发、成长。所谓“尽性”,即出于生命的自我需要而竭尽其能,所以是自生。总之,孟子、《中庸》都强调认知和把握生命本性对生生具有积极意义,因为认知和把握生命本性源自生命物的内在需要。荀子则认为,生命的自我认识包括“大我”,也就是对生命相关的所有事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都是有利于生生的。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荀子·天论》)在荀子看来,掌握宇宙万物的规律,才能顺利地、有效地养生、护生、成生。此处所谓“应之”,就是要求按照生命物的规律生生,从自然中获得资源以养生。王夫之也强调“自知”对生生的重要性,如果对生命处于无知状态,就不能使生命顺利成长。他说:“知天之理者,善动以化物;知天之几者,居静以不伤物,而物亦不能伤之。”【21】只有掌握了生命规律的人,才能善于行动而获得生命之所需,且彼此不伤害,并完善生命。人类作为灵性动物,可以帮助万物实现自生,这种帮助就体现在人通过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从自然中获取生存的养料上。戴震认为,人类异于其他生命物的标志之一,就在于能够认识、把握自然万象的规律,进而根据这种规律满足生命的“自然”需求。戴震说:“夫人之异于物者,人能明于必然,百物之生各遂其自然也。”【22】不难看出,儒家对于生命的自我认识非常重视,认为自我认识、自我反省对于生命的自我成长具有根本性意义,因为它可以不断调整、修正生生的路线和方向,可以找到生生中的弊端从而克服之,使生生顺畅地展开,使生生成就其所成就者。不过,这种自知、自省仍然源自生命物的内在需要,是生命物自我完善的认知表现,所以仍然是自生。生生之“自我认知”形式,所表现的是生命自我完善的自觉意识,是生命自我完善的精神内容,因而可被视为高级的自生形式。
基于上述讨论,似可作如下推论:“全自生”观念之于儒家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是因为:第一,如上陈述的“积极有为”之自生、“消极无为”之自生、“不同阶段”之自生、“他力辅助”之自生、“无形无相”之自生、“冬藏”之自生、“自我认知”之自生等,不仅说明自生的普遍存在,更重要的是反复证明了所有自生形式都源自生命需求。第二,生生过程中的所有自生形式,无不内含有自我成长、自强自通、自我调适、自熄自转,即指生命物之自生的自我成长、自强自通、自我调适、自熄自转无不源自生命物本身。第三,生生过程中自我成长、自强自通、自我调适、自熄自转等环节表现出循环性。比如自我成长,因为生生,必有成长,因为成长,必有服务成长,因而便表现出自我成长的循环。具体言之,因为生生而有满足生命的需求,满足生命的需求需要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管理,社会资源分配管理需要政府,政府通过治理体现自我成长,从而实现老百姓的自我成长,老百姓的自我成长反过来又有助于政府的成长。如此,自生之自我成长,表现为循环往复。因此,自生形式的多样性、普遍性、反复性,明示了“全自生”观念的客观性。“全自生”观念凸显了儒家主体意识的深邃性。为什么说“全自生”观念凸显了儒家主体意识的深邃性? 其一,自生是主体与本体的合一。自生源自生生之本能,所以是本体;自生是生生之功用,所以是主体。因而自生体现了主体与本体的合一,融主体于本体之中。其二,自生强调万物之生生,生、长、成、灭等环节皆自然而然。生生过程中所有的自生行为,自我生长、自我管理、自强自通、自熄自转等,都是自然而然的,但无不源自生命本身。其三,所有自觉的、非自觉的创生、养生、护生、成生行为,所有为生生的努力,亦都源自生命所需。其四,自生也可能为生生带来伤害,这种伤害称为“反自生”;而这种“反自生”可分“自觉的反自生”和“自发的反自生”,“自发的反自生”是积极的,“自觉的反自生”是消极的,对待这两种“反自生”需要用不同的态度和解决方式,从而显示生生主体的敏锐性。总之,“全自生”就是认为生生者所有关涉自己生的行为,都是自我发动、自我主宰、自我完善,而且是出于生命物的内在需求。正如刘因所说:“天地之间,凡人力之所为,皆气机之所使,既成而毁,毁而复新,亦生生不息之理也。”【23】所谓“凡人力所为,皆气机所使”,就是说,生生的任何形式的作为,消极的、积极的,善意的、恶意的,成功的、失败的,自觉的、非自觉的等,都源自生命物本身,从而淋漓尽致地凸显了生命物的主体意识。“全自生”观念蕴含了丰富深刻的意义。认识和把握儒家“全自生”观念有怎样的意义? 或许可提及如下几点:其一,自生是生生的本体形式。“全自生”向我们展示了自生的多样性、丰富性,但不管哪种形式,不管多么复杂,都源于生命的内在需求。这就意味着,“全自生”是对“自生”理念的充实、升华和澄明,“自生”是生生的本真、本体形态。既然所有生生都是“自生”,那么,一切与生命所以然没有关联的外生、他生以及造物主都只是虚设,进而对“生生”的某些误解,以及由这种误解导致的错误行动皆得以消除,“自生”理念得以确立。其二,自生是内在于生命的责任。所有“生生”形式都出于生命的内在需求,都是发出生命本能,创造生命、养育生命、保护生命、成就生命、尊重生命等,都是“生生”的自然行为,既不是因为天帝的命令,亦不是由于外力的迫使,因此,生命物是自我“生生”的主宰者。既然生命物是自我“生生”的主宰,那就意味着生命物对“生生”负有责任,“生生”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只能由生命物自己解决,而不能推卸责任。儒家“全自生”观念唤醒、激活了生生主体的责任意识,从而为推卸责任的行为设置了障碍。因此,发掘并确认“全自生”观念,对培养人们的责任意识具有积极的价值。其三,自生的成败乃生生自然。既然所有自生源于“生生”的内在需求,是“生生”之本然,这就意味着,“生生”过程中取得的成功或遭遇的失败,皆“生生”自然而无需计较。所谓“立功”是“生生”自然,不可居之,任何“自生”皆为“生生”本有而非外在,因而不应该将“立功”视为脱离“生生”的了不起的伟绩而感到骄傲。所谓“失败”也是“生生”自然,任何自生都由“生生”而发,但不是所有自生都能成功,消极、失败的自生是“生生”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插曲,因而对“生生”中出现的消极行为或结果,在态度上必须理解和宽容,在实践上必须进行自我调整或清除,此即善待“失败的自生”。其四,自生者必须竭其所能赞助生生。如上所示,成就“生生”的方式是多样、丰富的,而“自生”的本质是“生生”源于生命物自己。无论是“积极主动”的自生,还是“消极无为”的自生,无论是“不同阶段”的自生,还是“他力辅助”的自生,无论是“无形无相”的自生,还是“冬藏”的自生,抑或“自我认知”的自生,无不要求生命物穷尽自身的潜能,发掘并统合知识、体力、智能、德性等以服务于“生生”,从而使“生生”臻于完美。因此,“全自生”观念即意味着:大凡要成就“生生”者,必须竭尽全力发挥“生生”的潜能,此谓“尽性以事天”。
总之,“全自生”是儒家生生之学的一个重要且基本的观念,其精髓就是强调所有“生生”都是生命物的自我行为,而非外力强迫。即便看似被迫的行为,也是基于生命物出现了问题而展开生生的活动,因而所有有为的生生都是自生。这是最高原理。所谓主体、主观、积极等等,都是生命自然的行为,不是外在的,不是他力的。外在、他力的生生行为也都是由生命物及其相关的现象引起的。只有将生命物所有生生行为理解为“自生”,才能很好地理解和解决生命遭遇的各种困惑和问题。钱穆说:“中国儒家思想,认此宇宙为一整体,为一具体实有,在其具体实有之本身内部,自具一种生生不已之造化功能。既不是在此宇宙之外之先,另有一大神在造化出此宇宙。亦不是在此宇宙之内,另有一大神在造化出许多各别实然的人和物。宇宙间一切人和物,则只是此宇宙本体之神化妙用所蕴现。”【24】生命宇宙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生命内具生生不息的性能。生生过程中所遭遇的所有问题,都只能依靠生命生生不息地自我认知、自我调适、自我化解来解决。所有生命的本真在此,所有生命的真谛亦在此。
参考文献:
1. 参见李承贵《儒学“新本体”的出场》,载《河北学刊》2022年第1期。
2.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第七十八,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第2676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卷数、丛书名、册数与页码。
3. [明]王夫之《周易内传》,载《船山全书》第一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296页。
4.[明]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三,载《船山全书》第二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300-301页。
5.[明]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三,载《船山全书》第二册,第301页。
6.[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离合根第十八》,载《董仲舒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43页。
7.[宋]邵雍《皇极经世》卷十一,载《邵雍全集》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53页。
8. [清]颜元《赵盾第十六》,载《颜元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80页。
9.[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二十五,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2页。
10.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载《董仲舒集》,第176页。
11. [明]刘基《郁离子》,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70页。
12. [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载《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94页。
13. [清]戴震《孟子私淑录》卷上,载《戴震集》,第414页。
14.《朱子语类》有多处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释为“道体生生不息”。兹举几例:或问“子在川上”。曰:“此是形容道体。伊川所谓‘与道为体’,此一句最妙。某尝为人作观澜词,其中有二句云:‘观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无穷。’”(《朱子语类》卷三十,载《朱子全书》第15册,第1353页)问:“注云:‘此道体也。’下面云:‘是皆与道为体。’‘与’字,其义如何?”曰:“此等处要紧。‘与道为体’,是与那道为体。道不可见,因从那上流出来。若无许多物事,又如何见得道? 便是许多物事与那道为体。水之流而不息,最易见者。如水之流而不息,便见得道体之自然。”(《朱子语类》卷三十六,载《朱子全书》第15册,第1355页)“子在川上”一段注:“此道体之本然也。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朱子语类》卷三十六,载《朱子全书》第15册,第1357页)程子解“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曰:“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集注曰:“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即是此意。(《朱子语类》卷九十五,载《朱子全书》第17册,第3187页)。这些材料显示,朱熹以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对道体的描述,而且重其“不息无间断”“水之流易见道体”之意,即谓“道体生生”乃无声无息、无形无相也。
15.[宋]杨简《杨氏易传》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页。
16.[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十四《非国语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69页。
17.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四时之副》,载《董仲舒集》,第280页。
18. [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33页。
19.[明]王守仁《传习录下》,载《王阳明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1页。
20.[明]王守仁《五经臆说十三条》,载《王阳明全集》下,第980页。
21.[明]王夫之《读通鉴论·汉景帝》,载《船山全书》第十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117页。
22.[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载《戴震集》,第282页。
23. [元]刘因《游高氏园记》,载《刘因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7页。
24. 钱穆《灵魂与心》,长沙:岳麓书社,2020年,第127页。
本文原刊于《周易研究》2023年第2期(总第一七八期)
|
 当前位置:首页 > 新知速递 > 新知速递
当前位置:首页 > 新知速递 > 新知速递